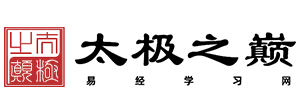諸儒-[清]胡煦撰《周易函書•别集•卷十三》
(清)胡煦撰《周易函書•别集•卷十三》篝燈約旨
周易函書别集卷十三禮部侍郎胡煦:撰
篝燈約旨。
諸儒
孔子之一字何等尊貴,曾子之明字何等確切,子思之中字何等渾淪,孟子之浩字何等擴大。
孔子猶天,顔、曾、思、孟,日月也;諸儒,星也。試以學、庸兩書較後世諸儒之所得,其淺深高下,當自豁然。
顔子之樂不易到,且學孟子集義之慊。孟子之義不易集,且學孔子時習之悦。學聖人之學,固當以孔、顔、思、孟為凖的。然孔之美富,猶天之不可階而升矣。曾之切實,猶覺太簡。思之深邃,猶覺高華。可以身體力行者,惟孟之集義養浩。四端充擴之語,近而易求。孟子曰:人皆可以為堯舜。期許不嫌太高,致功必先有據。吾竊有以私淑之矣。後儒之論說,有能如孟子之親切著明,愚雖不敏,亦當以瓣香奉之。
邵子之易,蓋亦極精極微矣,然皆圖象中領悟得來者也。故於經文未有註釋,或亦有不足者存乎?至其發明往來二字,亦有訛誤,後人引之以為註釋,學者泥而不逹,亦能使周易之實理不大顯露。至其有取於揚子,則非張子天分極高,但取資於六經,而有無隱顯交關處,實能見到活潑潑地,此豈中人以下所可能乎?至其詮釋經書,或亦有未當者存,然而長處不可掩也。
荀子性惡之說,憤詞也,欲其勤學以修禮立政,歸諸聖人之參贊耳,去揚子偽學遠矣。恐以氣質言性者,反不免有純駁之辨。
陸子天分極高,見地極超,後人信耳韙朱而貶陸,皆未嘗即二子之論而考其實也。
後人讀書,知有功名已耳。及語以聖人之學,則又高談濶論,褒貶古人。逮徵諸實見,不過然人所然,否人所否,胸中絶無確實把柄,要亦信耳者也。夫學聖學者,嘗數百年不一見,即如陸、王,亦可為聰明卓絶者矣。乃今之學者薄之,其薄陸、王者,又皆急功名,趨勢利,但學時文者也。豈陸、王之不子若乎?何不揣之甚也!須知朱、程、陸、王,悉皆孔、孟之徒,特其姿性有高明、沉潜之别耳。設此數人同生春秋時,要皆宫墻中人,未易軒輊者也。夫高明、況潜,兩不相能,亦易辨矣。必務争之曰:某者勝,某者負,某者是,某者非。即此必争之心,便非孔聖及門所有,但當辨别精粗,各存其是而可耳。
漢儒至董子而聖學始倡,即道之大原出於天一語,其原本出於中庸,而宋儒遵之,悉莫能外。今觀天人三策及繁露一書,儘有極精極微,非後儒所能及者。竊憶獨創之難,不似後儒共和之易也。今之議董子者,大約據天人三策而論之,至於繁露,未有輕置一語者,豈其未嘗寓目也?恐未能盡悉董子之意也。然而周子固開宋儒之始,而董子於羣言惑亂之時,獨倡為天人合一之說,董子之功偉矣哉!
董子曰:道者,所由以適於治之路也,仁義禮樂皆其具也。
又曰:設誠於内而致行之。
又曰:正其誼不謀其利,明其道不計其功。此皆扶持正學,極有見地者也。然其本領盡在繁露一書。
董子擇語:天積衆精以自剛,聖人積衆賢以自強;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,聖人序爵禄以自明。隂道尚形而貴精,陽道無端而貴神。欲致精者,必虚静其形;欲致賢者,必卑謙其身。我不自正,雖能正人,弗予為義;人不被其澤,雖厚自愛,不予為仁。孝子之行,忠臣之義,皆法於地,刑反德而順於德。天顯經隱權,前德而後刑。匿病者不得良醫,羞問者聖人去之。民無所好,君無以權也;民無所惡,君無以畏也。
揚子好奇而妄作者耳,徒以奇字奇解,惑亂天下,所以有太玄之作。究其實際,全無用處。豈知周易小用之而趨避之道在,精用之而性命之道在,大用之而位育之道在乎?太玄亦言吉凶,畢竟是不可試驗之吉凶,即其卦起中孚,畢竟非天根月窟之正理。自其依傍周易,另作一種法套出來,遂使後來好名之士,不顧道理之合不合,皆人人擅作者之場矣。豈知天下無二道,周易之外,不容更有周易,非以周易大中至正之道衡之,不可得而辨也。楊、墨充塞仁義,孟子曰:能言距楊、墨者,聖人之徒也。太玄亂易,甚於楊、墨,學孔、孟之學者,宜何如擯斥也?
玄之擬易,中說之擬論語,擬其辭之似耳。衡以大道,則索然無味。然論語之中,有克復之仁,有一貫之道,而彼何有乎?徒見其不知量耳。學者欲明至道,詳味六經,熟參四子書而已足矣。
馬融、王通、鄭康成、虞仲翔、荀慈明,皆傳經者也。王肅之兼義,雖未能盡合,而略例一書,則周易之大意已在其中,蓋見其概而未見其精也。
聖學至唐,亦已微矣。韓子之原性、原道,雖未盡醇,然而矯矯錚錚,固亦未可誣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