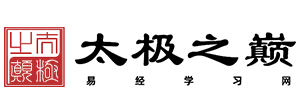性-[清]胡煦撰《周易函書•别集•卷七》
性
性也者,始亨之乾元,保合之太和,未發之達道,含仁蓄用之大本也。
性也者,定命之天也。
資始之乾元不可知,由各正之太和而知;賦性之天不可見,由所性而見。
言性而不本於天,烏知有中節之中?言道而不率於性,烏知有能中之節?
人物何性?各正之太和即其性。性何善?保合之太和即其善。故乾之文言稱善、稱嘉、稱和,皆善之繼也,太和之充也。繼善云者,繼此保合之太和也。坤之文言稱美在其中,即太和之各正也。所謂成性存存,道義之門者是也。
孔子言性渾而該,子思言性切而據,孟子言性確而真。孔子言元,子思言亨,孟子言利正也。言元者,長善之仁,各正之太和也。言亨者,發而中節之和也。言利正者,著見之四端也。
非有各正之太和裕之於中,則發而不中節矣;非有發而必中之具引而出外,則無由徵四端矣。桃仁不能生杏,杏仁不能生桃,其各正之性命殊也。孔子就其原本而証之,譬若含仁之桃核;子思據其源流而證之,譬若桃花之生桃實,桃實之生桃樹者也;孟子據其發端而證之,譬若桃核之生桃樹結桃實,必不生杏樹結杏實也。
性惡之說,憤激之詞也,欲人之勵學以踐形復性耳。善惡混之說,未察其原本者也。故荀、揚雖并稱,而荀之超於揚也遠矣。義理之性,氣質之性,兼善惡二端而文其詞,謂性中有惡矣,仍與荀、揚湍水同見,固不能為先儒諱也。
義理氣質之說,據一人而論,則與孟子性可以為善,可以為不善同旨;若據两人而論,則與孟子有性善,有性不善同旨。噫!之二說者,孟子固已確辨之矣。
孟子性善之說,証之於四端,由其大原本無差别故也。中庸分疏,知、仁、勇皆性中所自具,與四端之說無殊。其原皆各正之,太和始之,故孟子以為私淑諸人。
孟子証之於孺子入井,証之於孩提知愛,皆四德之端倪,太和之洋溢流通,著見發越者也。今有秦、越不相接見之人,驟而相值,必未有罵詈不絶于口,捶唾忽加於身者,可知和氣中存,善端之本裕矣。
人之一生,喜樂之事随時而著,無日無之。無端而怒氣之發,則數日數月不一見矣;可哀之事,又或一歲兩歲不一見矣。夫喜樂,和氣之徵也;哀怒,暴氣之徵也。由此言之,固可知和氣之中存,太和之各正,長善之理不絶于人心,性善之說不待辨而自明也。
常人之情,聞哀矜慈惠之語,則油然動其心,其動也,與本然之善兩相觸也;聞刻薄殘忍之言,則怫然變乎色,其怫也,與本然之善兩相忤也。此不但中人以上者然也,盗賊僉壬,倏而相感,莫不如是。至其轉念,或有不然,則習也,而非性也。故曰:性相近也,習相遠也。
和氣者,生氣也。乾元之所由資生,人心之所由中節,皆是故也。周易,言性之書也。論語,與門弟子問對交接之語也。淺學之士,未可語深,故曰:夫子之言性與天道,不可得而聞也。欲其深造道妙,則周易一書,固已詳言之矣。子貢聞之而莫能言之,曾子聞之而著為大學,子思聞之而作為中庸,非原本周易,烏能達此?
聖人不以心思知慮言性,是性之發也,天之動也。此乾元之日出而不窮,健行而不已者也。充其量,則耳之所聞,目之所見,莫非性矣。
聰明知慮,天之才也;参贊位育,性之充也。索其原,皆天能性能,而非聖人之能,故聖人無功。
天也者,萬物共有之性;性也者,人物各具之天。
乾言性也,坤以下皆言道也,周易言性也,四子六經皆言道也。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,則是子貢精契一貫之道,深達性命之旨,不待曰不可得聞,始見其妙悟之深也。天所以原性之始,道所以究性之終,是殆知夫子敎人最深最密,止此一性,一以貫之,則性中之作用也。春秋發天人感應之機,則性中之参贊位育也。周易發天人合一之旨,乾彖則天命之性,文言則率性之道也。天者性之大原,道者性之大用,故其下添一與字,均所以明性而已。故子思以未發者為大本,大本者性中之天也;已發者為逹道,逹道者性中参贊之作用,即天下歸仁之義也。顔淵問仁,子曰克己復禮,所復何禮,皆性中之事,故於其下即曰天下歸仁,謂大用之涵藴,其大無外者皆在此中耳。叔孫武叔章所謂美富,西銘之仁孝,皆此義也。如不說天下歸仁,止說性中所涵之大用,但以心同理同之說解之,豈知子思中庸全是言性之書,到了後半說出無窮大作用,難道皆性外之事乎?不知孔子、子思、孟子立言確不可易,徒令後來學者人人知有氣質之性而不察其繆,又不將一貫之道全身提掇,恐於聖賢立言本意未能發明。
自天以下,無物不具此天性,則無物不具此靈。卜用死龜,筮用腐草,此其證也。有形之器,無形之虛空,無往而非天性之充;則無實無虛,無往而非天靈之塞。龜顯于兆,筮驗于卦,此其證也。人之性,天之命也,唯虛故靈,故與天地同量。分海水之一滴,與海水同;分千燈之一照,與千燈同;分日月之一光,與日月同。
海之水,增一分無益迹,減一分無損形,藏天下萬派而不見其盈,日出以滋養萬彚而不見其乏。人之性,納千萬卷書,記無窮事,藏之於密而杳乎其無迹,感而遂通,應天下之萬變而浩乎其不窮。故唯海為可以喻性。感於視聼則妄,動於天則無妄。故無妄者,天之動也,所由曰率性之謂道。
性如原泉,其作用則江海也;性如桃仁,其作用則枝幹也。江海之泛濫,視原泉則藐乎小矣;枝幹之茂盛,視桃仁則渺乎小矣。然舍是則無由以發,故夫子曰一以貫之,子思曰率性之謂道也。
與萬物共此性命,故夫子之道在忠恕;為萬物培兹生氣,故居心之戒在刻深。
言天理,不若言天德。德者,實有於己之謂;理者,文彩外著之謂。理德不必同,行事之有得,始可言德。保合之太和,得於天矣。理文而德質,理虛而德實,理用而德本也。随處體認,便是說用邊之事。理曰天理,非遡原於天乎?仁心之存主,太和之各正者是也。如許大之天地,莫非太和所醖醸,故有化醇之說。人能存之,故久大與天地同量。孔子之敎顔子也,曰天下歸仁,便是此旨。天下歸,言仁中所藴之大也。
牛、馬、駒、犢初生,便知飲乳之所在,此真良知也。
凡人之生理,必隨氣而住,初未始無氣質。特理虚而氣實,切不可認氣為虚明之性耳。今觀農工商賈,終不免輕率鹵莽之氣。士子澤以詩書,便覺有雍容爾雅之氣。凡皆見於形體,徵於氣質者也。至於變易氣質,則虚明之性所能,非氣質之能也。如以氣質為虚明之性,則非。
後儒言性,必欲兼氣字,即有言得至當恰好處,亦終不免拖泥帶水。故言性而不取証於周易,未有不支離者也。子思、孟子一絲不走作,只是一貫之道傳得真,周易之理見得明。
聖人教人,必欲使人知為性善者,為識得受生之先,原不雜以偏邪偽妄,則適於聖賢之路,先已坦然順而且便。識得此中原自具有聖賢階基,則不自奮發者,便成自暴自棄。既欲使人知為性善,則惰慢自畫者,必將無可自委。解此,則天人合一,當必有凛然畏,惶然懼,悚然修省,而汗流浹背者矣。吾誠不解自宋儒以來,必欲兼言氣字,悞盡天下後世,是何心也?
孟子之好辯,為楊、墨言也。楊、墨各主一道,其不仁不義,皆在行邊,行故足以亂道,故孟子辯之。今之言性學者,乃在吾儒,既不克以外道目之,其著書立說,又皆以言,言則足以貽悞後世,而不止目前。乃其所言,又屬性分中事,又是行道之主宰。此處不辯正明白,致令天下後世怠廢自棄者,託於氣質以自諉謝,豈聖人教人本意?故予之嘵嘵不休,盖亦有不得已者存焉。
幾者,動之微,是乾元之亨字,中庸之發字。此時烏有善惡可言?如有善惡可分,則是所性中先已含有惡了。不然,何得幾之方動,便呈露出來?須知幾之方動,只當得孟子一箇才字,是能為善惡者也。中庸之發字,亦只是孟子之才字,只是性中發出之情耳。其情有七:喜、怒、哀、樂、愛、惡、欲是也。然此七字,只欲之一字無對,其下六字,皆相對相反而相因者也。因作七情圖。
欲者,念之動也。動而適意者三,自愛而起,適獲所愛則喜,常獲所愛則樂;動而拂意者三,自惡而起,適觸所惡則怒,久淹於所惡則哀。然是愛喜樂,和氣之發;惡怒哀,戾氣之發也。愛喜樂皆發於本心,順乎本心者也;惡怒哀皆觸于外感,拂乎本心者也。故遂謂為性善。
氣質為性之說,與孟子性善之說不相似。性即理也之說,與孔子窮理盡性至命之說不相似。天下歸仁之說,與孔子先難後獲之說不相似。性與天道不可得聞,以天道為天理自然之本體,與子思天命之謂性,率性之謂道不相似。以道為隂陽之所以然,與子思達道之言說在發後者不相似。隂陽是太極之用,因前有太極,故將隂陽說在道邊。道者,太極之用也,即在人之達道也。今以隂陽為形器,與孔子形而上者謂之道,形而下者謂之器不相似。姑擇而出之,俟知者考正焉。
先儒言學,有存誠、主敬、守静、致一之說,皆各從意念之最偏處而箴之,非此是而彼非也。故意念繁雜而紛擾,則主一之說為當;意念外馳而逐物,則守静之說為當;意念懈怠而外馳,則主敬之說為當;意念觸境而多妄,則存誠之說為當。
自伊川以下,龜山、李延平皆有主静之說。乃
朱子曰:静字較偏,不如主敬。謂敬可兼動静言也。朱子此言,是從中庸戒慎不睹,恐懼不聞看出。不知子思此言,是欲人立天下之大本耳。然子思不曰:喜怒之未發謂之中,敬則發後見之者也。既已敬矣,便是心有所用,未發之中何在也?故斷不可以主静之說為非。
静字妙於敬字,敬有操舍,静無來去。
經學近成帖括,不惟諸儒之書不能一一遍觀,深究其是非,其有略言道理者,旁人譽之曰:此程、朱之流。則亦儼然自負為道在是矣。吾誠不知達而可行者果何在也。
善惡有兩端,人心有兩用。思惡則霾昏霧障,而皎日沈光;思善則日白天青,而纎雲盡斂。
上一章节
下一章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