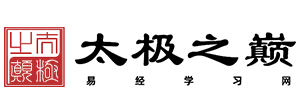張子-[清]胡煦撰《周易函書•别集•卷十二》
張子
張子西銘是言理一,不是言分殊。但解分殊中之理一,方能一以貫之。
張子西銘,從論語問禘章與中庸郊社之禮節及禮記萬物本天,人本乎祖并哀公問理會出來。觀其氣概,横塞天地,與孟子浩然同矣。其正蒙諸篇,則全從孔子繫辭與說卦理會出來。然細觀宋儒之書,要唯張子一人之論,全是理會易詞而出。
分之必殊,原不待言。即如一人也,耳、目、口、鼻、顴、額、輔、頤,無不同也,然終古無兩人相肖者矣。聖人之裁成輔相,皆是於理一上做工夫。子思之位育,說歸率性之道,孟子之萬物皆備,說出誠身之樂,皆是懼人徒知分殊而不知理一也。
帥字去聲,非入聲也,即孟子氣帥之帥,言為主也。
朱子曰:天理人欲之分,只争些子,故周子只管說幾字。然辨之又不可不早,故横渠說豫字。
張子天資最高,看他將化之與神,氣之與虚,兩儀之與太極打合一片,是何等見識!今將正蒙最精者標而出之。
張子擇語:散入無形,適得吾體;聚為有象,不失吾常。聚亦吾體,散亦吾體,有無混一之常,若謂萬象。
為太虚中所見之物,則物與虚不相資,形自形,性自性,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。
【煦】按:此謂形器資虚而立實,吾儒之的傳。若謂形器為虚,則同釋氏之論矣。要亦形上之道,形下之器二語,見得精耳。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,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。【煦】曰日光附月與地而始見,麗於虚則無由自見,是麗於實也。文理之察,非離不相覩也。方其形也,有以知幽之因。方其不形也,有以知明之故。【煦】曰此與周子動静互根同義。氣之聚散於太虛,猶氷凝釋於水。【煦】曰張子妙於言氣,本形上形下二語來,非氣則曷由形乎?由太虚有天之名,由氣化有道之名,合虚與氣有性之名,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。神者太虚妙應之目,【煦】之言靈,亦猶是也。兩不立則一無可見,造化所成,無一物相肖者。
一物兩體,氣也。一故神,兩故化。隂陽之精,互藏其宅。受者随材各得,施者所應無窮。木金者,土之華實也,其性有水火之雜。天體物不遺,猶仁體事無不在。【煦】曰,此則參贊位育不難。天之知物,不以耳目心思,然知之理過於耳目心思。聖人盡性,不以見聞牿其心,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。有不知則有知,無不知則無知。必物之同者,己則異矣;必物之是者,己則非矣。久者一之純,大者兼之富。易一物而三才,凡可
狀者皆有也,凡有皆象也,凡象皆氣也。至虚之實,實而不固;至静之動,動而不窮。
隂陽之義,張子所云一物而兩體者是也。
西銘不止言體,全是言用。其必從大原說出,是要人不可遽作分别耳。各正性命以後,天下之分殊,原不待言。張子本意,只是由其分之殊,推明理之一,使知生身之原,胥原於生物之大原而已。
【煦】按:知化則善述其事,窮神則善繼其志,志在事先,述在繼後。何謂繼?便是繼之者善。何謂述?便是體仁長人四句。其下承之以君子行此四德句,而曰乾元亨利貞,則述可知矣。張子本領只是得力於周易,遂令人駭其入理之深。
整菴羅氏曰:張子正蒙由太極有天之名數語,亦是將理氣看作二物,其求之不為不深,但語涉牽合,殆非性命自然之理。嘗觀程伯子之言有云:上天之載,無聲無臭,其體則謂之易,其理則謂之道,其用則謂之神,其命於人則謂之性。只將數字剔撥出來,何等明白!學者若於此處無所領悟,吾恐其終身亂於多說,未有歸一之期也。
【煦】按:此四句,首二句原不可易,即中庸天命之謂性。蓋氣化便是天之大用,各正之太和是也。其合虚與氣,便是言生人所受之性,長人之善,正在此中。只因宋儒有氣質之性一說,便將這箇氣字也看壞了。豈知性是虚靈的,氣只是形體,性必附氣而具,特不可認氣為性耳。至第四句則不能無弊,蓋性中未始不含知覺,性中却說不得知覺。必如孔子貞固足以幹事,方是說性中之含藴。繫辭又云:天地絪緼,萬物化醇,方是此時之事,便是其體謂之易。易之一字,便合天地間之大體大用而兼有之。自太極生出,至於有形有質之萬物,如男女居室,以及聖人參贊位育之妙用,非人之有也,皆易之用也,烏得專言體乎?道也者,大用之所在也,亦不得說在裏邊,看作所以然。
敬軒薛氏曰:張子曰一故神,即神無方。曰兩故化,即易無體。
【煦】按:兩者一之體,一者兩之神,故曰兩不立則一無可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