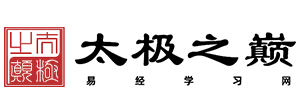河洛先天圖象(1)-[清]胡煦撰《周易函書•别集•卷四》
河洛先天圖象
孔子曰:河出圖,洛出書,聖人則之。既說在易經中,便是說則而畫卦。孔子
又曰:庖犧氏之王天下也,於是始作八卦。則是畫卦之聖人斷為伏羲明矣,則是伏羲之畫卦兼則圖、書明矣,可知洛書皆畫卦之資也。自向、歆父子及孔安國有大禹則書作範之說,後儒因有取於洪範、皇極,遂以洛書為作範之具,不取正於經文,而取正於先儒無稽之論,與孔子異矣。
畫卦聖人既指伏羲,伏羲又嘗兼則圖書,則圖書二者必同出於伏羲時,而伏羲必兼見此洛書,又無疑矣。乃後儒守向、歆之說,以為大禹時神龜出洛。今考尚書洪範篇,實無此語。此其異於孔子者也。或曰:孔子十翼並未有龜書出於伏羲之說,乃顧確以為然,何也?曰:孔子亦未有龍馬出於伏羲之說,然既以為庖犧畫卦,又以河圖、洛書說入周易,豈伏羲時神龜猶未之出乎?豈伏羲猶未見洛書之圖乎?豈孔子猶未考洛書之自,而漫入諸周易乎?豈文王本洛書而爲後天圖,武王獨未聞家教乎?孔子曰:天地定位,山澤通氣,雷風相薄,水火不相射。此釋先天圖也。細玩相字、通字,俱在流行圓轉處說,獨天地定位一語,似言對待耳。然而上天下地,其閒化育流行,實無一息不克相通。即在先天圖中,雖若分天上地下之象,然陽之始終必交于坤,隂之始終必交于乾,是位雖定而氣則通,原在流行處立之象矣。又其一陽二陽三陽,一隂二隂三隂,何非圓轉不息,流行活潑之機耶?觀下文數往者順,知來者逆,忽用此往來字面,豈其不相流通,而有此往來之順逆耶?今以為先天對待不移,夫先天則未發之中,活潑潑地,有何對待之可拘乎?此其異于孔子者也。
孔子於先天圖止有天地定位數語,未嘗取其圖而改易之也。河圖洛書是天地自然之易,一為先天,一為後天,確不可亂者也。文王後天之卦,倣象洛書,是方位之一定,所配則發皆中節之和。伏羲先天之卦,倣象河圖,是内合而外分,所配則未發之中。洛書在有象之後,故有定向,故可紀以卦位。河圖在無聲無臭之内,有何卦之可執?况此時河圖雖出,伏羲尚未畫卦,有何卦之可配?又况河圖所寓,止有畫卦道理,亦必非卦所能配。又况伏羲畫出,先天止有圖象,以内合外分之機,象生成比附之妙,此時尚未開而為卦,亦復有何卦之可配?乃後儒解說河圖,顧以文王所開之卦拆而補之,強與先天之數相配。先天而可拆也,猶得為先天乎?卦而可配先天也,不成兩後天乎?失先天之旨,昩後天之序,與孔子異矣。
帝出乎震一節,言後天圖也。其必始震終艮,而貫帝字于上,所以明乾陽之布濩,即大明終始之義也。周易貴陽,于此可見。然不能移離于震前,移兌于乾後,是則時位之一定而不可易者,即寓此圖中。今反以為流行不息,與孔子異矣。
孔子于先天圖,則但言其相通相薄,初未嘗分卦而言之,明未發之無可分也。于後天圖,則各就其卦中所置之位,與位中所得之卦,一一分别言之,明已發之無可合也。而今顧反其說,謂先天一定而不移,後天流行而不息,與孔子異矣。
隂陽太少之說,是伏羲熟玩圖書,因取其中所藴道理則以畫卦,知二圖之數不踰奇偶,而天下萬事之理不越隂陽,因畫兩儀以象之。又玩内生外成之理,爰復各加两儀,遂成四象。自此至于六爻,無非两儀之加,而千變萬化由此殊矣。因四象各具兩儀,于是乎有太少之别,是則隂陽太少乃畫卦時初加再加所定之名目也。乃後儒不以四象為畫卦所定,執隂陽老少之說以解河圖生成之數,豈知河圖所具止有此理可為取則之資,而實未有此名可配生成之數也。今乃欲取而配之,與孔子異矣。
凡有一圖,必有一圖之妙,故不宜移動絲毫。孔子曰太極生兩儀,兩儀生四象,四象生八卦,為先天小圓圖言也。既有生者,必有成者,是即則圖本旨,是即與河圖相配之故。今執拆補之說,而不究内生外成之妙,與孔子異矣。
先天配未發之中,後天配已發之和。孔子曰:易無思也,無為也,先天之静體也,乾之元也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,後天之動用也,乾之亨也。先天在無思無為之地,有何可拆?必如拆補之說,是未發之中而亦可拆為喜怒哀樂也,與孔子異矣。
大衍之數五十,其用四十有九。此處孔子不言太極,非無故也。蓋太極無形,非可言說。今既有蓍,則有形矣;既云五十,則有數矣。有形有數,故不云太極,直從兩儀說起,而曰分而為二以象兩也。且伏羲之圖由兩儀而起,未有太極也;文王之卦由乾坤而起,亦是兩儀邊事,未有太極也;周公之爻由初之九六而起,亦是兩儀邊事,未有太極也。皆為太極無可言說,故從可言者起也。今必添說除一以象太極,太極何形而亦可象乎?與孔子異矣。
孔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,又曰一隂一陽之謂道,則隂陽為形上之道可知。今曰卦之隂陽皆形而下者,其理則道也,是直以隂陽為形器之具,而未知隂陽在太極初亨之會,有理而無質,故孔子謂為太極生兩儀。至兩之生四,乃始云象,象謂有象之可指耳。即乾彖之釋亨,指出流形之義,非形器也。即至後來生出八卦,亦不過剛柔太少之再重耳,亦非形器也。聖人作為連斷之形,畫出重交單拆之象,亦不過倣象隂陽變動之理,究非有形器也。夫由兩儀之生而至于八卦六十四卦,尚非形器,安得執兩儀而遂謂形器乎?形器可見者也,隂陽之在天地間,可形見乎?今謂隂陽為形器,與孔子異矣。詳見篝燈約旨。
孔子韋編三絶,假年學易。若止因占卜之事,便費如許苦心,則占卦固如是之難乎?且孔子終身學之,止成得一卜筮人,猶得為孔子之學乎?今曰周易止是占卜之書,異矣。
周易,傳道之書也。孔子曰:易冒天下之道。
又曰:道義之門。
又曰:其道甚大。
又曰:和順于道德。
又曰:三極之道。
又曰:易有聖人之道。
又曰:彌綸天地之道。
又曰:形而上者謂之道。
又曰:為道也屢遷。
又曰:立天道,立地道,立人道。是周易為傳道之書,何等精深!何等奥妙!皆由伏羲圓圖之虚中,與文王之乾元,周公以初命爻及乾元无首之旨而出。今謂周易止是占卜之書,竟使學者視之,與術數無别,亦異于孔子矣。夫占卜亦周易所有,特周易之支流,而非傳心之正旨也。
周易,言性之書也。河圖未發之中,洛書已發之和也。圓圖之内合則其中也,外分則其和也。文王之元亨利貞,由未發之前而推及于已發之後者也。周公之爻,已在既亨以後,而始成之一爻,命名為初九之既用,又以為无首。是皆欲人由已發之後,而追尋乎未發之初耳。故于繫說諸傳,既以為盡性逹天,又以為察來也。其乾之彖傳,由資始之元說到保合太和,却止是天命之謂性也。其文言傳,由長善之元說到貞固幹事,却止是率性之謂道也。凡皆已發未發之真詮也。後面于始亨之利貞說出性情兩字,于得朋之坤說出美在其中,何非性善之的旨?子思、孟子蓋有所本矣。今曰周易止是占卜之書,異矣。
周易,窮理格物之書也。今觀其中所引天地、日月、風雨、雷電、山川、水火、草木、禽魚、馬牛、羊豕之類,無所不備。至其分見于各卦各爻,其象亦各各不同。即有偶同者,亦不必皆同一義。彖、象、文言,格其物,窮其理,莫非有益于身心性命之事。今但以為占卜之書,異矣。
周易,博文約禮之書也。經之與傳約二萬餘字,乃上而仰觀天文,下而俯察地理,近取諸身而人事之悉備,遠取諸物而巨細之不遺,其文亦已博矣。而要其旨歸,莫不有大本存焉。晰至精至變之象而歸諸爻,合至變至精之爻而歸諸卦,合至紛不齊之卦而歸諸四象兩儀,合四象兩儀而歸諸虚中之太極,則逹道在是,大本在是矣。孔子曰顯諸仁,是彰往而極博者也。又曰藏諸用,是察來而反約者也。然博易而約難,故曰其上易知,其初難知也。今但以為占卜之書,異矣。
周易,天人合一之書也。孔子曰:易與天地凖,故能彌綸天地之道。
又曰:範圍天地而不過,曲成萬物而不遺。
又曰:裁成天地之道,輔相天地之宜。是參贊位育之妙在易中矣。
又曰:與天地合其德。
又曰:成位乎其中。是天人合一之旨在易中矣。即在卦爻取象,非據天道,則援人事,謂天人合一而已。今但以為占卜之書,徒向趨避進退、周旋交接上留神,曾未察天人合一、至精至微之道即在其中,與孔子異矣。
聖人寄占卜于周易,非徒欲天下後世有前知之道也,亦謂占卜之妙,析于幾,本于太極,通于神明,非逹性天而明于幾者不能,此便是教人最深最妙之旨。今但以為占卜之書,異矣。
大傳曰:形而上者謂之道。
又曰:一隂一陽之謂道。則是孔子明謂隂陽為形上之道矣。蓋太極為大道之本體,其中含藴,非圖可畫,非言可說,而流行之中,隐隐有此二端,往來進退,盤旋幹濟于中,其所生之物,有形無形,莫不具是,實不可以形迹拘也。聖人目之為道,蓋以其方出于太極,有理而無質,故察其流行活潑之妙用,而命為隂陽云耳。所由既謂為形而上者,而又謂為道也。既謂為形上,則非形器之重濁者可比;既謂為道,則又散見于萬物。
本義曰:卦之隂陽皆形而下者,其理則道也。是以理為形上之道,而以隂陽為形下之器矣,與孔子異矣。無論太極之體至靈至虚,其出不窮,原非理之可言,即此隂陽方從太極而出,唯其至靈至虚,運化太極之大用,然後能流行變化,充塞兩間,生成萬物而不有其能,變化萬彚而仍无其質。今謂隂陽為形下之器,夫器則有形可觀,而隂陽何形之可觀?器則有體可據,而隂陽何體之可據?陸子辨之。至連用四十字,如寒暑、上下、晝夜、晦明之類,皆無形之隂陽,尚未能察識。其不詳察人言中之意,亦已甚矣。至陸子謂朱子昩于道器之分,
朱子答曰:若以隂陽為形而上者,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?據此看來,則並未知物之所以為物矣。中庸鬼神章,固孔子之言也。其曰體物而不可遺物,即形下之器也。其體之者,則隂陽也。朱子嘗註為集註,亦以所體之鬼神為隂陽,不聞以所體之物為隂陽也。其下又云:來書所謂始終、晦明、奇耦之屬,皆隂陽所以謂之器。夫始終何形乎?晦明何形乎?而謂為器乎?此皆異於孔子隂陽為道之說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