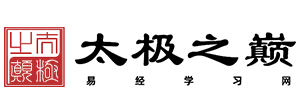孟子-[清]胡煦撰《周易函書•别集•卷十》
孟子
孟子曰性善,先儒兼氣質而言。許函谷嘗語崔後渠曰:性譬良玉,善則其温也。此語最有領會。無有玉而不温,自無有性而不善者。今兼氣質而言,則子思發皆中節之說,與孟子性善之言為不當矣。學者平心自思,必有分曉,安得屈思、孟而崇後儒耶?其必兼氣質而言,不過誤看性相近也一語耳,遂有幾善惡之說,而後世相因,未能改正。豈知相近之說,止對相遠而言,由其後之大相懸殊,而追索其初謂為相近。相近云者,只如云不遠云耳。後邊說上智下愚,不說賢不肖,原在天資明昧上說。盖賢不肖皆有為立事之後所分别之品行,而智愚則據性之所發而言也。既是說性之發用,便是說習。如人初生,便解飲乳,便解視聽,此良知也。然壯年知識便與孩提較進矣,老年知識便與壯年較進矣。同焉此人,一讀書,一不讀書,其知識明昧又大相懸絶矣。同焉受業,一用心,一不用心,其知識多寡又大相懸絶矣。則明之與昧,因習而殊,亦較然矣。聖人言此,原要指明學者逹天徑路,端在學習有以變化之耳。又以見習染之汚溺而不知返者,非其本性然也。其正意全在言外,兩兩對勘,便可知由習反性的妙理。豈謂初生之始,便有些子不同乎?孟子嘗言之曰:氣,體之充也。豈有充體者而認為虚靈不昧者哉?
孟子工夫最密者,無如集義;見地最高者,無如萬物皆備;功之最大者,無如性善;効之最切者,無如浩然;事業之光顯,無如正人心。非身親做出,何能說出!
孟子具參贊經濟,只正人心一語耳。觀其以羊易牛,宛轉相引,皆正心之妙也。若其好色好貨之說,雖未甚確,皆是從君心上宛轉引掖者也。
子思之言性,以命之于天者証之,故不待言善而先有以觀其繼矣。孟子之言性,以驗之于情者証之,故必言善而後有以原其始也。然由大本而率為達道,則情之不爽不待言矣。說仁義而以為根心,則從出之源頭亦可識矣。
性善之說,匪特與告子辨論極其精詳,如孺子入井,孩提知愛,皆極親切。覩親,仁也,固不待言;敬長,義也,便成人亦是如此。鬩牆之兄弟而外禦其侮,不仍是不忍之心油然生乎?所由謂仁統四端,兼萬善也。孔子以大哉獨贊乾元,而文言以為善長,便是此旨。
常人之情,聞哀矜慈惠之語,則油然動其心;聞刻薄殘忍之言,則怫然變乎色。所性本善,盖可知矣。此不但中人以上者然也,盜賊僉壬,莫不如是,特轉念不然耳。是習也,而非性也,故曰習相遠也。
羊舌氏狼子野心,出左氏傳,與孟子有性善、有性不善之說相似。然孟子固已確辨其非矣,後儒不察,猶引以證性,何也?
樂善者,聞言而喜,彼在中之善為之招也。如是久久,惟見其慊,投之以非所樂,則不覺其相忤,故嘗有惄然不安之情。即大不善之人,其初豈便若此?只是集之既久,其勢既盛,不覺反客為主耳,所以謂為性善也。孟子以好善許樂正子,善而果好,則集義之勢於是乎存,慊心之機於是乎在,故許之。顧善之在人,集之難;不善之在人,集之易。坤之文言所由曰:盖言順也。
直養塞天地,此即中和位育之妙也。天下歸仁,正在於此。子貢之美富,亦是如此。如但以空虚之氣,便爾能塞。彼世間匹夫之勇,剛愎自用,其氣亦能塞否耶?故下文
又曰:配義與道,無是餒也。須知禮樂刑政,能塞之具也;裁成輔相,能塞之用也;下文義道,則能塞之本也。然觀一配字,豈不說在行上?觀下文集義、行義之說,豈不說在行上?然而性善之妙,即在於此。
功名念重,利禄横塞胸中,非此不快。然而彼之慊,則此之餒矣。皆所謂反客為主,習而安焉者也。其實止知字一關未能打透,天之一字未見分明,集之一字未能履到實地,遂不免為庸衆之歸耳。豈必窮凶極惡,然後謂非聖賢乎?然而些小之善,不到慊然地位,究不克為聖賢。甚矣,集之難也!
孟子集義,即顔子克己復禮之功。己,外也,故曰克;禮,内也,故曰復。猶不安其室而復歸者然也。孟子曰:非義襲而取之也。
又曰:仁義禮智,非由外鑠我也。其告子之内仁而外義也。孟子曰:義非外也。故孟子之義,即顔子之禮也。是已離室家,旋旋招集之說也。但顔子之復,七日之復也;孟子之集,是敦復無悔者也。
集之亦易易也。長善之德,具於性初,觸之而動,則貴其有行,行而得,斯謂之德。逮於觸之,而時時動於善矣,非此不快矣,斯慊矣。為惡而無忌憚,必有慊心之時;樂善而不倦,亦必有慊心之時。此與時習而悦相似。
善之集也最難,惡之集也最易。集善難,故孟子著慊心二字;集惡易,故孔子於坤之文言便曰:盖言順也,言其勢之甚便而已。何也?人之為惡,不要有心去做,但只消因循苟且,曰:不大傷害無窮之惡。集之何難?惡之積也既易,則善之積也亦愈難矣,故孟子鄭重言之。
一事之勉致,恒覺其苦,苦非順也;一時之偶爾,旋即於忘,忘非慊也。慊也者,坦然暢然之致也;集也者,不一時不一事也。便是孔子自志學以至不踰矩,皆慊也,皆其集焉者也。顔子非此莫之好矣。
長。善者,吾心之德;慊者,吾心之自樂也。故曰:非外也。惡人之集不善也,非其性然也,其初亦嘗試之而偶為之耳。試之而無他也,有甚於此者,而亦嘗試之矣。又試之而無他也,有更甚於此者,而亦嘗試之矣。逮於窮凶極惡而不可返,斯為惡人,斯亦集而後有者也。故孔子於坤之初爻,特著順字之說,謹始慎微之妙也。夫天下窮凶極惡人,豈皆習而安焉者乎?或有欲而不窒,或有忿而不懲,嘗試為之,其心必有不安者存。殆久而忘焉,再蹈前轍,其心仍必有不安者存。至於罪大惡極,牢不可破,雖平旦之氣,亦必仍有不安者存,斯其不快亦已甚矣。故能慊之心,必歸諸集義之人。
人皆可以為堯、舜。孟子此言,豈不太高?今人上看朱子,便不敢輕易議論一字,况聖人乎?竊謂今人之自待薄矣。顔子曰:舜何人也?予何人也?有為者亦若是。孟子曰:堯、舜與人同耳。後人不明性善二字,遂覺聖人是天地生成的一般。苟具此心,將不流于匪僻僉壬而不止矣,宜其不敢于先儒輕置一語也。然德之不修,不克學有為之顔子,徒恣其狂誕,妄擬古人,則又先儒之罪人也。孟子之私淑,畢竟有可以自信之處。今人自思,果何者為可以自信者乎?子思曰:率性之謂道。
又曰:發而皆中節。孟子曰:非由外鑠,則率性之謂也。孟子曰:性善,則發皆中節之謂也。此其所由自信者歟?故以為私淑也。仁義禮智,非由外鑠我也,我固有之也。
又曰:天下之言性也,則故而已矣。與孔子文言元亨利貞之旨同義。凡鑠之者,皆在外者也。火之鑠金,非金之本有也。鑠之久,而金之全體皆火也。聲色貨利之誘,詖邪偽妄之參,非性也,習也。陽明以為良知,允哉!知而不良,外之鑠,習之遠矣。故孔子曰:習相遠也。
程子謂:康節講易,儘說得好聽。
朱子曰:此便是程子不及孔子處。然朱子于子靜之卒,哭己曰:可惜死了個告子。朱子此言,恐與好聽之說相似。門人未察其實,于是謂孟子闢告子矣。
告子,孟子之弟子也。後來荀、揚如性惡、禮偽、善惡混之說,皆各執一見,終身不易。而告子則往復辨論,不憚煩瑣,又且由淺入深,屢易其辭。安知最後無復有言,不既曉然于性善之旨乎?今人謂告子諸章皆告子之言,其言固屢易其說矣。安有自謂知性,曾無定論,猶向他人屢易其說者也?屢易其說,則請益之詞也。今觀其立言之序,其始杞柳之喻,疑性善為矯揉,此即性偽之說也。得戕賊之喻,知非矯揉矣,則性中有善可知矣。然又疑性中兼有善惡,而為湍水之喻,此即善惡混之說也。得摶激之說,知性本無惡矣,則又疑生之謂性,此則佛氏之見也。得犬牛之喻,知性本善矣,則又内仁而外義。及得耆灸之喻,然後知性中之善如是其確而切,美且備也。此皆一節節打通,一步步入奥者也。若非節節打通,步步入奥,烏得始終各異其辭,淺深各異其見乎?今知讀書窮理,以文章取功名止耳,求寢食不忘,諄諄性學如告子者幾人?甚矣,告子之未可量也!顧乃以孟子為闢告子,何耶?
論語稱子者絶少,子貢、子張,其字也。有子、曾子,門人之稱也。箕子、微子,襲古之稱也。顔子亞聖,猶稱其名。萬章、陳臻、充虞、彭更、公孫丑,皆稱其名。而告子、樂正子、公都子,獨以子稱,其非異端明矣。觀其諄諄向性學打點,則其稱子也固宜。或者不察,謂為闢告子,誤矣。豈其既知性中有善無惡,又知仁義皆不待外求,反不若後儒義理之性,氣質之性,變善惡而文雅其詞者,為得解乎?後儒之論,有不可盡遵者,此例是也。今人讀孟子書,若但章章分看,則以為闢也宜矣。如必合前後而較量之,則其前後淺深,當必有辨。蓋人之論人,有論世之法,而人之誦詩讀書,亦須有誦詩讀書之法也。
形色天性,是以性釋形,即孔子藏諸用之旨也。仁者人也,是以形釋性,即孔子顯諸仁之旨也。何形非性?何性非形?孟子私淑諸人,其深契一貫之妙,深逹發皆中節之旨歟?子思之大本達道,歛位育于中和,皆是之故也。思、孟以後,則形性分矣,一貫之所以難也。夫形色天性也,此語惟孟子道得出,後儒則道器之分,諄諄不休矣。夫龜之朽骨,蓍之腐草,聖人用為前知之具,此何義乎?不知血肉草木無情之物,皆天地之靈化所生,故至濁亦含至清,至蠢亦含至靈,至無用皆含有用。故遠祖之骨,亦可以福至遠之子孫,則天下之塊然不靈者,莫非天靈之運化,蓋可想矣。
天下之本在國,國之本在家,家之本在身,而獨不言身之本,廣土衆民章言之矣。仁義禮智根于心,本,幹也,根則本之所由以生,枝葉之所由以茂也。晬面盎背,則一身之事,而幹與枝葉自不待言。若不培其根,則不慊而餒矣,烏能晬面盎背,逹于家國天下而稱浩然乎?孟子繼往開來,得稱亞聖。惟在性善二字,于楊、墨則闢之,以其充塞仁義也;于告子則辨之,明其似是之非也,非闢也。後世讀書窮理,用為博名之具,乃至夤緣奔競,無所不至,則仁義之充塞甚矣。性命之學,絶不挂口,其亦見棄于告子矣。若使告子而司性學之衡,政恐入選者蓋寡。
程、朱以後,言性學者,或廣取諸家之說而示之博,或獵取先儒之論而莫之斷,竊懼好名之過甚,而窮理之未精也。夫羣言淆亂,則衷諸聖,要當以孔、孟為之主耳。告子之不動心,雖由強制,特屈于孟子一人。如第縱吾心之所欲,而不求所以不動,若告子強制,亦胡可多得哉!
盡其心者,知其性也。知其性,則知天矣。此與孔子窮理盡性以至于命、子思天命之謂性無異,皆是一脈相承,原原本本,確有根據。今于盡心知性中間添必由二字,竟是知性在未能盡心以前。試問古今來有不窮理而能盡心者乎?試思知其性也與下文知其性三字有異乎?無異乎?若說作兩様道理,謂知其性方能盡心,知其性方能知天,則是不必盡心而亦有知天者矣,必非孟子相承說下之旨。若將兩個知其性說作一様道理,則盡心精而知天細,又必不能強合,豈孟子相承說下之旨?須知此說即窮理盡性至命之說。蓋窮理是初學時逐事逐物求明工夫,盡心亦是如此。盡字與窮字相似,都在用功一邊說。特窮也者,不極不止之謂,盡亦求到極處之說。天下何理不具于心?故盡心便是窮理之至。性也者,此理從出之大原也,故盡心到極處便能知性。天也者,又心性之大原也,故知其性則性中所涵之天不待言矣。用一則字,說得極便易。蓋天即在性中,未有不知天而可謂知性者也。既知天在性中,而曰盡其心者必由于知其性,則是知性知天皆在盡心之前。既已知性知天矣,尚欲盡心,亦何所冀乎?
程子曰:孟子有大功于世,以其言性善也。孟子性善養氣之論,皆前聖所未發。
【煦】按:善,推其所為之說,亦前聖所未發。
龜山楊氏曰:孟子一書,只是要正心
【煦】按:孟子正心之說,從周易文言來,故確乎謂性為善。而孟子絶大本領,可以參贊位育者,只正人心三字耳。
朱子曰:易言繼善,是指未生之前;孟子言性善,是指已生之後。
朱子曰:未發時,怵惕惻隱與孩提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,少間發出來,即是未發底物事。靜也只是這物事,動也只是這物事。如孟子所說,正要人于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,即是靜時所養底物事。靜時若存守得這物事,則日用流行即是這物事。而今學者且要得動靜只是一個物事。朱子此論,方與孟子之性善、孔子之一貫相合。解斯義也,立則見其參于前也,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,豈有異道乎?然而靜中之含藴,實不可量。如當愛當敬者,發出來本是兩様物事,而愛則仁也,敬則禮也,二者原不同德,二用亦不必同時。然當發而為愛時,而敬之理仍在中也;當發而為敬時,而愛之理仍在中也。有形之物,實而取之,則其器虚矣。而性獨不然,故曰天下歸仁。
雲峰胡氏曰:孔子亦嘗說性善,曰繼之者善,成之者性,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,不從人性禀受處說。子思曰天命之謂性,率性之謂道,正是從源頭說性之本善,但不露出一善字。性善之論,自孟子始發之。蓋生不是性,生之理是性,天地間豈有不好底道理?故曰渾然至善,未嘗有惡。古今只是一個道理,故曰人與堯舜初無少異。孟子道性善,言其理也。稱堯舜以實之,言其事也。天下無理外之事,能為堯舜所為之事,便是不失吾所得以生之理。然而人不能皆堯舜者,氣質之拘,物欲之蔽也。
【煦】按:繼善之善,從造化說,不從禀受說,此語最佳,深合乾彖與文言之旨。蓋乾之元即乾之善,故當其亨時,所由謂為溥美利于不言也。文言說人性之元,亦即以善長稱之,本乾元之善而立言也。唯乾元為大善之聚,故其于各正也,亦遂以太和言之。保合者,自其命賦而言也。繼此善以成其性,即保合之太和而已。故其在人,亦遂以元為善長,即所繼以成性者也。子思有見于此,故說出率性之謂道。孟子私淑諸人,故斷斷乎謂性為善,皆其原于孔子者也。繼善之善,性善之善,止此一善,原無分别,安得曰性善之說自孟子始乎?
敬軒薛氏曰:孟子言性善,實自繼之者善來。因繼之者善,故性有善而無惡。
朱子曰:孔子尊周,孟子不尊周,如冬裘夏葛,飢食渴飲,時措之宜異爾。孔孟易地則皆然,
【煦】按:春秋時,五覇迭興,臣強君弱,漸有驅制同儕,决裂臣道,渺視周君之意,是君權將替,而臣道已亢。故孔子作春秋,寓意于尊周,所以維持臣道也。孟子時,七國雄據其地,強悍自用,臣道亦已不振,而草菅民命,各圖恢擴。故孟子遊齊梁,說以王道,所以維持君道而已,與孔子非有異也。孟子曰:乃若其情,則可以為善矣,乃所謂善也。若夫為不善,非才之罪也。前曰情而後曰才,何也?情也者,性之動而靈明者也。事無鉅細險易,皆一情之動用為之。人知為動用之能,而不知其實原于性,故孟子遂以性之動用處命之為才。此如太極為本,一亨而為隂陽,後面兩儀四象,以及六十四卦,備萬物之數者,莫非隂陽動用之能也,故孟子遂謂情為才。予所由謂仁義禮智為天德,其行此四德者,即天才也。
日出而不匱,充塞而溥被,太和之能也。充于形骸,逹于四體,人始有動用之能。孟子曰:形色,天性。蓋有由然矣。
又曰:不能盡其才。離性而别有才歟?至于瞽者善聽,聾者善視,跛足者善倚,皆其形使然,非性之然也。解此,方知氣質不可以言性。
龜山楊氏曰:孟子處世衰道微之時,使楊墨之辨息,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,無父無君之教不行于天下,而民免于禽獸,則其為功非小矣。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,亦足為知言也。
【煦】按:世之止知功名,而挾詐營私,不知上下之義,與楊氏之無君何異?釋氏之無倫,則較楊氏而更甚矣。頋世之禪學,猶有人焉嗔之詆之,而顯然冒于楊氏者,乃在學士大夫,可不慎哉!
問:孟子露其才,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?
朱子曰:亦是戰國之習。如三代人物,自是一般氣象。左傳所載春秋人物,又是一般氣象。戰國人物,又是一般氣象。
【煦】按:宋儒又是一般氣象。試看孔子之門人便知。蓋孔子之門人,各各欲成就真實本領,絶無一個知有聲名的,絶無一個向言語中自行標白的。
雲峰胡氏曰*:孟子是義精理明,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,告子之不動心,是硬把定,是麄法強制而能不動。
不二注:原为“五峰胡氏”疑似有错,今改之。
【煦】按:告子亦是戰國時亟欲留心性學之人,止被朱子說作孟子闢告子,便把告子說壞了。倘其時人人皆如告子,縱未到聖賢地位,安復有縱横堅白之人擾亂天下?今試將告子幾章接連看,便當知告子矣。觀孟子養氣章,盡舉告子之不足處而是正之,何嘗直薄其為人?况時至戰國,孟子而外,有幾告子乎?
慶源輔氏曰:人說孟子論性不論氣,若以生之謂性章觀之,亦未嘗不論氣也。
【煦】按:生之謂性章,便是說告子言氣之非。
雲峰胡氏曰:孔子亦嘗說性善,曰繼之者善,成之者性,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。子思曰天命之謂性,率性之謂道,正是從源頭說性之本善,但不露出一善字。性善之論,自孟子始發之。
【煦】按:何嘗發自孟子,乾彖已詳言之,子思已明述之。今止援繫辭繼善之說,而不援乾彖太和之說,是仍未知太和保合是所性之大源也。又曰人不能皆堯舜者,氣質之拘,物欲之蔽也。
【煦】按:說物欲之蔽則可,說氣質之拘,是仍說有氣質之性,萬不可也。
敬軒薛氏曰:孟子知言,亦本于孔子不知言無以知人之說。孟子言知言,即孔子所謂知者不惑,其言養氣,即孔子所謂勇者不懼。又曰易言繼之者善也,此善字實指理言也。孟子言性善,此善字虚言性有善而無惡也。然孟子言性善,實自繼之者善來,因繼之者善,故性有善而無惡。
【煦】按:實自乾彖來,孔子子思一脉之傳也。今人不先攻透周易,而遽爾言學,皆無本之學也。若知性善出于太和,則以氣兼言亦可,然亦止是善氣,並無惡氣,觀其特提出和字可知。
敬齋胡氏曰:孟子發夜氣之說,于學者最有功。盖心也,理也,氣也,一也。心存則氣清,氣清則理明,理明則氣益清,氣清則心愈存。其要在操存省察于旦晝之間,不為物欲所汩。
【煦】按:必將氣與習辨得明白,方知真性。今之所謂性,皆外面之物染耳。
又曰:孟子所以有功于天下後世,是提出一個性字。其所以闡明這性,是點出一個善字。
【煦】按:子貢曰夫子之言性,不可得聞,是就其教門弟子言也。至周易一書,則全言性矣。孔子學之,韋編三絶,可知文周聖聖相傳,皆是如此。從而上之,精一執中,亦是如此。今人不打透周易,安知孟子有自來乎?
周易函書别集卷十
<經部,易類,周易函書約存__周易函書別集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