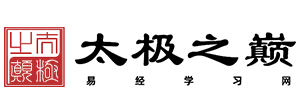論語-[清]胡煦撰《周易函書•别集•卷十》
(清)胡煦撰《周易函書•别集•卷十》篝燈約旨
周易函書别集卷十禮部侍郎胡煦:撰
篝燈約旨。
論語
論語如太和元氣,該貫渾淪,諸賢則各露圭角矣。但以忠恕兩言熟看大學,便知論語之包涵迥異,此聖與賢分别處。
曾子、子思、孟子,大賢也,然其立論,要皆見得明,說得定,而實能垂教,有功百世者也。夫格、致、誠、正、修、齊、治、平,後世有能出其範圍者乎?天、性、道之旨,子貢以為不可得聞,而子思聞之,又有中和之訓,位育之能,費隐之機,誠明之旨,精及于無聲無臭而莫測其端,察及于鳶飛魚躍而莫知其故,大及于上律下襲而莫窮其際,妙及于川流敦化而莫窺其神,後世有能出其範圍者乎?孟子集義以養浩,前此有言之者乎?驗諸情而徵性善,前此有言之者乎?正人心以回氣運,前此有言之者乎?此孟子之所發明,後世有能出其範圍者乎?大學、中庸,孟子之書固在也,凡皆深造道妙,各有真見,故其立論不必盡同,揆於聖人精一之傳,總無違忤。若先儒所闡,如存誠、主敬、守静、致虚、格物、窮理諸說,凡皆四子書中所已明,比諸先賢特闢蠶叢,獨抒己見,實能與聖道足相發明者,不少概見,此又先儒與聖賢分别處。
敬軒薛氏曰:夫子所謂一,即統體之太極也。所謂貫,即各具之太極也。
又曰:天以一理而貫萬物,聖人以一性而貫萬事。
【煦】按:貫字止是充周之義,只當得發而中節之發,和為逹道之逹字耳。一貫之說,己見前卷。
朱氏文炳曰:一貫忠恕,體用而已矣。曾子于此著明之,而于大學又推廣之。修身以上,所以體此忠也,一之所以為體也;齊家以下,所以行此恕也,貫之所以為用也。此一貫忠恕,為聖賢相傳之心法也。
敬齋胡氏曰:一貫即體也。蓋人之一心,萬理咸備,體也;隨事而應,無不周遍,用也。曾子平日戰兢臨履,忠信篤實,則其心之本體己立;隨事精察,無不詳盡,則其心之大用已周。所謂一貫者,固在其中矣。故夫子一喚即悟,不然,則應之必不如此之速。其後子思發明中和,以為中也者,天下之大本也;和也者,天下之大用也。
程子序易曰:體用一源,顯微無間。皆此道也。
述而不作,信而好古,竊比於我老彭。孔子之聖,豈其不能作乎?今觀六經,如詩、如書、如禮,删定纂修之而已矣。春秋固魯史也,孔子之春秋,筆削之而非作也。易之有翼也,固所以發三聖之精藴,非易外創為不稽之論,如後世之太元軌策,京、焦輩自為一家言也。自太元作俑,為易外之易,後世好名之士,不顧其驗與不驗,可用不可用,遂競以著作名家。今不盡去後世之偽書,不盡焚後人之偽作,則周易之旨,不可得而明也。聖人之道,止有六經,六經之外,猶且不作,六經之中,猶且非聖人之自作,則後世所有之書,其為不經也明矣。大約作者之弊,始于後人之好奇而喜新,不知舍六經而言道理,皆非正理,故議論必以近古者為正。夫今人之聰明不逮古人,即一二事可以觀矣。古之樂舞,窮神而入化矣,而今之韶、夏、大武,猶有存乎?古之瑟,動天地、感鬼神矣,今之瑟已失傳,有能復為古瑟者乎?今之琴音,能一一如古琴乎?今之龜卜失傳,有能創為龜卜而一一可驗者乎?古之鍼灸,古人已作之藝,既已失之,猶不可以復得,况能作乎?况有精深于此,非伎藝之比者,而顧作之乎?噫!何陋也?何愚也?而猶復自用,抑又何也?即如龜卜之法,史遷所著,以為死龜。漢去古未遠,史遷必有所授,而宋、元以下,乃有執為活龜者。此皆好為奇論,以欺天下者也。不盡去天下之偽書,周易之理,不可得而明也。何也?天地之間,不容有二道故也。後世之書,有最不可信者,如兎本胎生,顧以為吐而生;燕之來去,隨氣而化,乃以為伏于水。此其說之可聼而實悞者也。至風雲月露之詞,全無道理,人人藉此以博名高、稱詞翰矣。不揆于理,而肆于文,是理之蠧也。孔子于周末,已有文盛之感,若見後世之作,宜何如傷悼乎?
子曰:蓋有不知而作之者,我無是也。蓋知由聞見而入,圖、書既泄以後,其資人聞見不少矣。已知而益求其知,聖人之所以為生知;不知而無以為知,愚人之所以終無知也。無知而不自知其無知,此所以妄作而不自諒也。後來儒者,自子雲作俑始,而洪範之牽引洛書,致亂聖人之經,較子雲尤甚。今試平心静慮而觀之,洪範本文,固未有洛書之說也。武王請益于箕子,而洪範因恃以不廢,以其所明皆天人合一之事,與周易同旨故耳。至于洛書,文王固凖之以為後天圖矣。武王親承家訓,豈其不解洛書乎?豈其不解洛書為周易中後天之用乎?乃顧以洪範為本于洛書,而請益于箕子,則是文王之家教不具,而武王之承受不的。夫朝夕親承,猶不能盡探厥旨,彼偶爾之詞說,便悉解乎?不察其原,顧以洛書為作範之具,則是有聞而不之擇,有見而未之識也。如是而作,為有知者乎?亦異于孔子矣。
天下歸仁,言斯仁之藴,包含難量耳。猶云天下之大,皆在一仁含藴之中,是即元為善長之理。元而既亨,後此之善,皆由元出也。朱子謂天下皆與其仁,豈有纔去克己,天下便以仁許之乎?且人而與我,便可為仁;人而不與,便不可為仁乎?若但以為心同理同,即不作如此說話,于克己者亦復何損?且孔子之教顔子,只言己身之事,何與他人事,而言不切己之效乎?其教樊遲,尚曰先難後獲,豈其教顔子也,而顧以其效歆動之乎?此等道理,不可不明。
天下歸仁,與子貢之美富,孟子之萬物皆備,子思之致中和,天地位焉,萬物育焉同義,即乾彖萬國咸寜,文言美利天下之旨也。張子西銘皆由此出。今謂天下許我以仁,則非教以為仁之旨矣。夫顔子所問,固自治之仁,非治人之仁也。孔子之教,惟仁字最精最微,是性命之大原也。如但以理同心同之說為訓,與一日克復有何關涉?況必說到天下許我以仁,然後討探出心同理同之旨,亦大費曲折,非立言之旨矣。
孔子上承先聖,下開來學,止一仁字,是天之賦而具于人,敦萬化之源而為含生之主宰者也,故曰天下歸仁也。
仁也者,一元之長善,保合之太和,成性之大本,衆美之會聚也。就天而言之為元,即方賦而言之為太和,即所禀而言之為性,統天人而言之為道,合性道而一之為仁。長善之理既裕,然後為善由此而生;大美之聚既精,然後衆美由此而盛。孔、顔之樂,樂此者也;孟子之集,集此者也。
仁之本源,授于天命而生機不息;仁之周遍,逹於事物而無往不存;仁之流通,貫于今古而無時不然。其粗則驗于居處行立之中,其精則通于性命天人之合。是則仁也者,即聖聖相傳之道,而孔子之及門所諄諄考証者也。淺者淺言之,樊遲、司馬牛是也;深者深言之,仲弓是也。然猶在門戶上把持,非入室之事也。克復之訓,則入室之事矣,然猶在將違時著力,所謂不遠之復是也。而仁之本體,究未有能啟其機,俾得盡力闡揚,顯然呈露者,其庶求于天下歸仁之一語乎!解此,則一貫之一,生理之直,太和之保合,與體仁長善之理,皆在是也。克己復禮,如不解性量之大,但以為自己一身之事,與釋氏坐禪、楊氏為我何異?豈知一貫之道,即在天下歸仁一句中,此方是聖道不同于異端處。仁即一也,天下歸即貫之具也。唯天下歸仁,然後可發而為逹道。子貢曰:夫子之言性不可得聞,宗廟百官之美富不可得見。皆此仁之含藴也。子思之參贊位育,語大莫載,語小莫破,造夫婦,察天地,發育峻極,持載覆幬,皆此仁之措施也。孟子之塞天地萬物皆備,皆此仁充周之量,不盡之藏也。今但曰天下許我以仁,與克復之義有何干涉?即令人不許我,與克復之我又有何損?當知歸仁一語,聖人之參贊位育,盡在其中。
子貢曰:性與天道,不可得聞。朱子謂:性者,人所受之天理;天道者,天理自然之本體。夫既以為天理矣,又謂天理復有本體,然則天理為存主者乎?為達用者乎?如以天理為存主之事,則是存主之中,又復有存主者矣。如以天理為用邊之事,然而聖賢之言性,從未有說在用邊者也。觀此,則性學之不明也宜矣。須知此語止是說性而已。天所以原性之始,究性之大本也;道所以極性之量,究性之大用也。故於天道之上,添一與字,皆本性字之說而言之也。
曹月川曰:克己復禮為仁,是孔顔所傳之心法。吾道一以貫之,是孔曾所傳之心法。夫聖人之心法一也,何所傳之旨不一歟?盖一是仁之體,貫是仁之用。
【煦】按:此等解說絶佳,盖貫之一字,即天下歸仁之妙也。
聖賢無浮泛不切事理之言,周易非曠邈不可稽考之語,皆須從自身上體貼。晉人清談,畢竟濟得甚事?據有識者看來,直謂為無人可耳。學者但能為一時所尊貴之人,一時所尊貴之事,而不能為古今所尊貴之人,古今所尊貴之事,非具眼者也。
性相近也二章,是言習也,非言性也。因見世間窮凶極惡之人,其初亦未必如此,故曰性相近。因所習殊途,後遂流極而不知返,故曰習相遠。習而相遠,謂非生來便如此也。如此說,方與子思率性為道、孟子性善之旨相合。盖思、孟皆學於孔子者,豈思、孟謂性本善,而孔子言性反謂其中有些子戾氣乎?固知合義理氣質以言性,畢竟非孔子之旨。即下章上智下愚,亦是指習後而言,非性之定也。天下豈有生而聖賢、生而僉壬者哉?其習於上而為智也,至此則不可移矣。苟非上知,一轉移之,未必不可以為惡。其習於下而為愚也,至此則不可移矣。苟非下愚,一轉移之,未必不可以為善。此夫子教人慎習之旨也。然天下窮凶極惡之人,亦必皆極聰明、極伶俐之人,而今謂為下愚者,謂其心志陷溺邪僻而不知反也。自來解此一章,謂為夫子之言性,錯會相近二字之旨,故以義理氣質言之。夫性而可以氣質言也,則是性中亦有不善者矣,豈不與孟子、子思之言相逕庭乎?夫思、孟固有所授而然也。今試看論語二十篇,並無一語言及性字,故子貢曰:夫子之言性與天道,不可得而聞也。子貢身在聖門,日聆聖訓,猶以為不可得聞,今謂此二章是夫子為性而言,則誤之誤也。
相近之說,原自習學之後,推本於命賦同原之意。今以義理氣質分而言性,謂義理之近於氣質乎?謂氣質之近於義理乎?是二之也,非近也。求其說者,須於乾之彖傳文言中,精察繼善成性,體仁長人之故,方始得解。性相近,習相遠,非謂相近之中,猶有些子差錯也。因見後此之習染,大相懸絶,故追遡其初,而以為相近。相近云者,如云非遠云耳。然其止言相近,不曰一致者,此理自具乾卦。盖乾之元亨利貞四字,全是說賦畀之事,便是天命之謂性。體仁四句,全是成性之事,全是發皆中節之事,便是率性之謂道。然由元之一亨,直至於貞,始曰各正性命,則是萬物之有性命,是元亨之既定,萬物已得所資,各正其體,保合於中,乃始立之名耳。夫乾元固萬物之太極,至一而不分者也。到得各正性命,已在萬物上見得其中有人物之分,靈蠢之異,已非乾元渾合一致不分之時。夫物而萬矣,各正其性,則性命之不一審矣。不謂為相近,而謂為一致,能乎?聖人之語,極有分曉,特人不察耳。繫辭固曰:繼之者善也,成之者性也。善則一元之長,是至一者也;性則萬物之各正,是不一者也。今於不一中而追遡至一,故但以相近言之。況人為萬物之靈,與物不同,以人較人,安得不謂之相近?是打合儔衆,比量較論之詞。不知此旨,則相近之中,便說有些予差錯矣,非孔子之旨也。
羊舌氏狼子野心之說,是左氏之妄言,非聖人之正論也。夫學者立論,不取正於六經、四子書,依聖賢大中至正之論,而獨取左氏不經之談,以為人生本有氣質之性,致貽悞天下,貽悞後世,則悞之悞矣。夫左氏之書,所紀皆春秋中事,大約皆魯春秋之副本耳。魯之春秋,固聖人依為褒貶,而不取其正文者也。故知其文久為聖人所棄,乃後儒猶悖理而取之,何也?夫豺聲之說,固婦人之言也,豈男子之智反不婦人若也?即以今時之談論証之,所說不經,而談言微中,亦或有之,豈遂以為常乎?况遂據之以論性乎?
惟上知節,是舉習之極深而不可摇動者,以見其相遠之實也。性體正静而虚靈,何有知愚之可分?其得以智愚分見者,習也,而非性也。其習于率性之本而不移于近也,故以為智;其習于汙染之極而不移于遠也,故以為愚。智也者,擴其虚靈之體而牖之者也;愚也者,蔽其虚靈之體而溺之者也。一習也,而智愚之分遂若天淵,是愚之自遠于知也,故以為遠也。夫習而既移其性矣,故習宜慎也。孔子此兩章及子思天命之謂性章,與孟子性善之說不大為改正,則性道二者終古不明于天下。
學日益增,而其智日開,則從前之愚可知。愚而自用,習之所以日遠而莫移也。孔子曰:我非生而知之者。盖言其實也。今人以聖人為天縱,因致自畫,抑亦不思之甚矣。
孔子稱顔氏為不遠之復,相近而習於近也。不移者,習而遠也。見非下愚,皆可反而習于近矣。
子生三月,非無知識,謂為智愚,皆不可也。向後漸長,知識乃日開耳。故智愚者,習後之懸殊也。譬諸盜賊,壯年以後,無所不為,豈其初生一歲半歲,遂知有盜賊之事乎?
譬諸孩提初生,養於深山之中,日與樵夫牧豎為儔,則彼所知,唯樵夫牧豎耳。終其身不見美色,終其身不聞雅音,彼亦烏知有紅裙之悦目,宫商之娛耳哉?若使偶一見之,偶一聞之,此等種子,一入於心,眷戀而不舍,至於獨眠静坐時,胡思亂想,必將虚靈之地,廣大如天者,全然占却,使本來之善,無地以自容矣。由此加之以習,予誠不知何所究竟也。又如孩提之生,未必遂知為盜,偶見他人竊人之物而取之,而亦竟取之矣。初遂嘗試為之,而人不之責也。從而習之,漸可以偷矣。由偷而習之,漸可以劫矣。由劫而習之,便可以白晝截人於道。此豈其生性使然哉?亦習而日遠,至於不移故耳。
何以見智愚之為習也?孔子於乾之文言歷指性中之德,謂元為仁,亨為禮,利為義,至於貞而獨不言知,何也?智也者,性之發而後見者也,故但以事幹二字發明知之根原而已。盖此四語皆是言性中之德,故但云足以。足以云耳,非竟有仁禮義之可指也。孟子四端字說在惻隱之上,便是文言証據。此節既分知愚,又分上下,則是其中便有箇相遠字。既說相遠,便可知其是說習,不是說性。
習也者,聖學轉移之一大機也。性習之解不分,昧於性則聖學之大本無稽,昧於習則聖功之轉移無術。既言智又言愚,既言上又言下,謂言近乎?謂言遠乎?如以為言近,則不應有智愚之懸絶,又於智愚之中復有上下之懸絶。如以為言遠,則是此節斷斷乎言習,非言性矣。
孟子以時稱孔子,以智字說在聖前,以為貫始終之事。此即孔子言智、仁、勇,必先說智字之義。盖必見徹始終,然後依次而行,方克無悞。知在行先,亦是此旨;見得明,然後守得定,亦是此旨。文言之亨,止說事榦,非由見得極明,何以為事之榦乎?盖智與四德,雖同具一性之中,非徵於事為,必無可見,故獨居四德之後,直以為事榦,而不言智。然天下有作有為之事,非見之極明,則行之不去,故獨居事先,而以為事榦。然但為事榦,則仍非有作有為之時矣,故於此不提智字。政以智愚之分,必從事上見出,性中縱涵此理,當其未發,原無可分,故曾子援引聖經,但及明德。據本體之虚靈而言,智之本也;孔子以為事榦,此之義也。陽明有見於此,故極力闡發良知。
性者心之主,此不動者也。凡知之既萌,皆動後事也。故人但有智愚可分,便不是言性。
凡人生之聖狂異路,善惡殊軌者,非其至性然也,性相近也,習乃相遠耳。凡習染之未甚深者,皆可轉移,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耳。
離卦外陽,火之光也;内隂,火之質也。虚火不能自立,故必附質而有明,所以為麗。邵子火用以薪傳,正為此也。日之光亦附地而明,若麗於虛,則無由以自見矣。故晝日之明,因地而有,麗於實也。夜則地面無日,而空虚之中,未嘗無日。明麗於虛,必無自見之義。故離上於地,則為明之晉;離下於地,則為明之傷。離與他卦相配,則無明可言,正此義也。今人之知,涵於心體,亦至虛耳。然作之於事,而智愚始可以自見。故孔子之文,言於元,言仁,於亨,言禮,於利,言義,於貞,宜可以言智,而但曰貞固足以幹事,言智之本體而已。論語中上智下愚不移,是從事上得見,故有智愚之可分。智愚既說在事上,則是言習之遠,而非言性矣。若性則元善之長,以虛為體,有何智愚可言乎?因性學不明于天下,故性相近也。兩章皆不知為言習而發。
問:不遷不貳如何?呂涇野曰:不遷怒,發而中節之和。不貳過,幾于喜怒哀樂未發之中。顔子逐日在這性情上用功,怎麽不謂之好學?又問:何以見得性情?曰:七情之中,唯怒為甚,怒而不遷,則凡七情皆得其正矣。人性至善,本無過失,過而不貳,則馴致于至善矣。
【煦】按:聖人之學,止有治情之一法,存養省察,戒慎恐懼,皆其事也。其最易弛者無若怒,故顔子不遷,而夫子稱之。最易忽者無若好惡,故大學一書,自誠意章便以好惡言之,推之則心正于好惡,身修于好惡,而家齊國治天下平,亦莫不釐正于好惡。好惡既正,而猶有過者,未之聞也。曾子曰:仁以為己任,不亦重乎?死而後己,不亦遠乎?此便見得仁之為量,統四德,兼萬善,天下之大,盡歸仁中,非其既聞一貫,未易解也。
水之為性,增一分無益迹,虧一分無減迹,盈無盈迹,消無消迹。分一為萬,而分之迹不可尋;合萬為一,而合之迹不可辨。達人觀之,可以悟性。子在川上,當别有難言之妙旨也。逝者如斯,謂道體周通而無滯,靈之妙也,即所謂無方體也。不舍晝夜,謂道用日出而無窮,虚之妙也,即所謂無窮盡也。
坦然行之而無疑,位置曲當而無悞,非至明者不能。故智者不惑,在仁、勇之先。若或稍留疑義,則惘然無辨,疑畏不前,何能做出仁、勇!
智天覺,仁天德,勇天才,皆性也。謂誠之幾為善惡,然則此三者,非一性之發而分見者乎?而亦有惡之可稱乎?孔子曰:五十而知天命。
又曰:假我數年,五十以學易。周易固盡性達天之學也。論語中引詩、書者多,引周易者少,所由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,不可得而聞歟?
子貢曰:不見宗廟之美,百官之富。孔子之富美如不在論語中,則子貢之言無據矣。若其富美即在論語中,則曷不於論語求之?子貢曰:夫子之言性與天道,不可得聞。不可得聞,即不見富美之說也。一以貫之,猶之乎不可見也。夫子之語顔淵曰:一日克己復禮,天下歸仁焉。此富美之實也。若解為天下許我以仁,將富美之實盡行埋却,不知天下歸仁是說天下之大,盡歸吾仁度量之中,此正富美之實,一貫之的旨也。今方從自己身上做工夫,而便曰天下許之,學者平心自思,有是事否?志於道一章,原重道字。道也者,大用之所存也。志也者,通前後本末而矢諸心也。體諸身,通諸性命,所以究道之本也。達諸才,徵諸事業,所以充道之用也。今人輕看游藝,非也。夫子以博文教顔子。人生無窮事業,非材不足以達之,儘有修身慎行,立心醇茂,究其作用,無一可稱者矣。聖人之多能,所以儲參贊位育之具也。
顔子仰瞻鑽忽四語,本言道體,朱子以無窮盡、無方體釋之,深得其妙矣。程子謂曾點、漆雕開已見大意,大意果何存乎?觀斯未能信之言,則開之確見無窮盡也。觀三子之志在出,曾點之志在處,則不獨用時有道存矣,是點之確見無方體也。因二子所見各得一偏,故以為大意也。程子之解如是,故愚謂宋儒之解一貫者,獨程子耳。
無窮盡者靈而虛,無方體者虛而靈也。若靈之何以虚,虛之何以靈,則聖人亦不能自言其故矣。故伏羲之畫圖也,必不能畫太極。文王之卦,但從乾、坤而起,不能說乾、坤以前。周公之爻,但說二用,不能說九六以前。孔子之釋元也,但云資始,而元字之實義,到底不能分疏。其釋筮數也,但云分而為二,而未分以前,到底不可取象。所由一貫之一,聖人心會之,曾子意解之,到底不能多置一言。忠恕一語,亦周易取象之遺意耳。
子貢曰:夫子之言性與天道,不可得而聞也。非其既聞,終不知有此事,何由知為不得聞也?
又曰:不得其門而入,不見宗廟之美,百官之富。非其既得入門,親見其所以然,何由知其中有此等美富也?此與孔子天下歸仁一語相似。一貫之傳,曾子而外,斷當以子貢為首。新安陳氏曰:顔子博文,精也;約禮,一也。
論語中諸子皆止問仁,唯子貢與顔子獨問為仁,然所問亦有不同。子貢全問在作用一邊,故夫子以利器為喻,旋以切磋砥礪之法告之。顔子所問則極精極密,而而全體大用俱在者也,故以克己復禮說入極精極微本然之地,旋復以天下歸仁告之。見此極精極微之地,而經綸參贊無窮之大用即此而在。人知求為于作為之地,而不知大用實原于大本,故天下歸仁一語特為為仁言耳。曾子、子貢,夫子嘗以一貫語之,顔子聰明遠過諸賢,此即夫子以一貫教顔子也。誤解作效,則不達此旨。
孔子之教仲弓也,曰: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子貢曰: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,吾亦欲無加諸人。乃孔子固曰非爾所及,何也?蓋其教仲弓,是因事省察,故教之以勿。而子貢之言無,便是極濶大極渾成的,故孔子云然。
篇章詞賦之學,務博求于名人之風雅,描寫花様,期于肖似,故日弛于外;性命道理之學,務深求于聖賢之心志,返觀内照,求慊自心,故日專于内。弛于外,常懼他人之不我美,故常侈衒赫之光,久則必將好名,而夤緣粉飾之術由之以起;專于内者,常覺我心之絶與人殊,故時具闇然之意,久則常不自足,而隱微深幽之地亦愈難安。
集註言不屈于欲,此四字最妙。凡人莫不具貴高之性,誰甘受屈于人?不知妄念一動,隱伏中甘為所屈而不辭,仔細思之,能不恧然自畏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