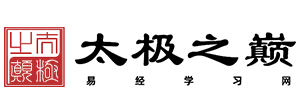道-[清]胡煦撰《周易函書•别集•卷七》
道
道也者,性中之大用,天命之充周,廣大精微,内外如一,顯微無間,形形而不役於形,色色而不役於色者也。道之原本在性天,則其大用可知;道之充周在参贊,則其原本又可推矣。謂道為形器之所以然,則子思性天之說置於何地?謂道為形器之所以然,則子思参贊之說又是何物?觀中為大本,則大本是中,不是道矣;和為達道,則達在已發後,不是未發者矣。
易曰:成性存存,道義之門。存存,静而涵之者也。以道由存存者而出,故以存存者為門,非以存存者為道也。存存者,性也,非道也。其曰形而上者謂之道,形而上則動而發越之時,非存存之時也。其曰一隂一陽之謂道,一隂一陽則太極之已動在兩儀一邊,非太極静正之時也。惟道在發越之後,故大而經綸参贊,小而一技一藝之微,均遂得以道稱之。
子曰:誰能出不由戶?何莫由斯道也?由則行邊之事也。夫子之道,忠恕而已矣。忠恕則人已交接之事也。吾道一以貫之。貫者,道用之充周,故謂為吾道一,非道也。其指出一字,乃發明不可思議之源頭耳,故門人不能解會也。子思曰:君子之道費。是專說用邊事。下面方說而隐,是因道之大用而推道之所以然,仍在大用中見出,與孔子因貫而說一相似,非以道為大用之所以然也。又如夫婦、天地、子臣、弟友、行遠、登高、發育、峻極、闇然、日章諸說,為言大本乎?為言大用乎?若為言大用,則道之未達,必另有所以然者在也。若於中庸解為猶路,便將道字看死了;若以為形器之所以然,又將道字看在大本裏面去了,均非道字之的旨。
聖人之言,本不欲文,不欲深,務使人人易曉。聞其語者,愚夫赤子皆可洞然解釋。獨天、性、道三字,非天性既明,不可以言道;非天道既明,不可以言性;非性道既明,不可以言天。此六經、四子書中最精最微者也。所由謂聖人所傳之道,非但言語章句便可通曉,故曾子唯而門人疑,而子貢亦以為不可得聞也。
道為充塞天地物事,其所以然,則隐而不可知。充塞天地,故其用最廣;乃不可知,故其體最微。孔子一以貫之,正體用一如之說。子思曰:君子之道,費則充塞天地者也,隐則不可知者也。語大莫載,語小莫破,正充塞之大用,而其所以然者,則隐而不可知也。子貢之不可得聞,蓋言隐也。孟子浩然之氣,配義與道,正與子思費字同旨,正謂道之充塞難量,而吾身之氣克與之配也。若謂隂陽為形器,以道為形器之所以然,則將道字占却大本地位,與隐字相似,無以見道之充塞而費矣。如謂道為充塞之物,為形器之所以然,而道之隐處又另有所以然,則是牀上安牀,屋上架屋矣,亦不得專以費處為用,隐處為體。程子曰:内外一如,顯微無間,是本末流通之妙,一貫之旨也。中庸之言費而隐,皆此旨也。若論其實際,則斷在大用充塞一邊。
太極者,道之大本;兩儀、四象、八卦由此而漸分者,道之大用。伏羲畫圖,但從兩儀而起,太極之中,一無所有,而其出不窮,不可名言,不可圖畫者也。其由兩儀、四象、八卦然後始達於用者,明大用之實出於大本,而大本之實發為大用。此正察來彰往,微顯闡幽之妙,所云本末流通,隐在費中者,此也。文王開為六十四卦,孔子之彖傳,每卦之往來,胥說圖中之妙,每卦之内外,胥說先天之旨,故曰周易為傳道之書。
道也者,参贊之妙,位育之能,裁成輔相,曲成範圍,皆其妙用也。其事則禮樂刑政而已。後之學者,開口言道,便趨向不可知不可說處,非道之真指也。参贊位育,裁成輔相,聖人之道也。下至於農圃醫卜,射御術數,極鄙極䙝,極微極細之事,莫不各有一道存焉,故曰道之用廣。遺一道,非道也;見一道,非道也。大道不器,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,子思亦曰體物不遺也。
子曰:朝聞道,夕死可矣。所聞者,形上之道也。若但執器而言道,安見其可以死乎?
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相傳之道,皆見諸行事者也。文、武以後,道不行於天下,孔子起而修明之,何非修齊治平之道可見於行事者也?觀於三月而魯國大治,聖學之美富可知。漢、唐以後,孔、孟之道衰而弗振者凡二千年,至宋儒起而振之。然觀周、程之政事,司馬之通鑑,邵子之内聖外王,張子之西銘,莫不各有達而可行之道。聖門學者,如愚魯辟喭之倫,大都惟處則修行,出則致用之為兢兢。故顔子亦有為邦之問,而勇藝明逹,莫不各就其所長。若無真實作用,將位天地,育萬物,與天下歸仁,萬物皆備之道,恐不解幹辦此事。
上一章节
下一章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