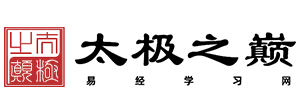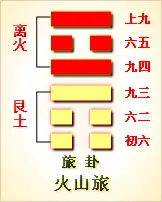【周易十翼】系辞•上传-[宋]胡瑗撰《周易口义》
[宋]胡瑗撰《周易口義》繫辭上
周易言繋辭者,按周易始于伏羲,畫為八卦。至于文王,定為六爻,演為六十四卦。又作卦下之彖辭,以解釋一卦之義,曲盡天地之道,總包萬事之宜。而又周公作其爻辭,以釋逐爻之義。然而聖人作卦,其道至大,以至纎至悉之事,无不備載。雖有爻彖之辭以解釋之,然其辭義深遠,其理精微,至淵至奥,不可以易曉,則于常常之人,固難知矣。是故孔子復作十翼以釋之,欲使後世之人,可以達聖人之淵奥,知聖人之行事也。所謂十翼之名者,曰上彖、下彖、大象、小象、文言、上繋、下繋、說卦、序卦、雜卦。凡此十翼,以釋六十四卦之義。上、下彖以解文王卦下之辭。大象以釋一卦之名義。小象分于六爻之下,以解周公之爻辭。文言以文釋乾、坤二卦之理。此繋辭以統言天地之淵奥,人事之終始。說卦以陳說八卦之德業。序卦以序六十四之次叙。雜卦以辨衆卦之錯雜。此上繋是夫子十翼之中第六翼,自天尊地卑而下至篇末,分十一章,各列于後,今隨文而解之。然按先儒周氏云:上繋辭凡十二章,自天尊地卑為一章,聖人設卦觀象為二章,彖者言乎其象為第三章,精氣為物為第四章,顯諸仁、藏諸用為第五章,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為第六章,初六藉用白茅為第七章,大衍之數為第八章,子曰知變化之道為第九章,天一地二為第十章,是故易有聖人為第十一章,子曰書不盡言為第十二章。虞飜分一章,以大衍之數并知變化之道,共為一章取之。然分義之段數未盡意,隨文而别解之。然繋辭有二說,是聖人繋屬其辭于爻卦之下,故此篇第六章云繋辭焉以斷其吉凶,第十二章云繋辭焉以盡其言。是繋者,取其繋屬其辭于卦下,故謂之繋辭也。
天尊地卑,乾坤定矣。
《義》曰:此言天地之道者也。自此乾坤定矣,而下至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為一章,以釋聖人法天地之義也。夫易之所始,始於天地。天地之判,混元廓開,而萬物之情皆生于其間。既萬物之情皆生于其間,是故聖人仰以觀于天文,俯以察于地理,于是畫為八卦,以類萬物之情,以盡天地之道、人事之理,以盡乾坤、水火、風雷、山澤之象,是易之卦始於天地者也。然則天尊地卑者,何也?夫天是純陽之氣,積於上而為尊;地以積隂之氣,居於下而為卑。剛陽居上,而有尊高之象;柔隂居下,而有卑下之分。二氣始交,分為剛柔,是以交錯以至生成萬物,覆載萬物,大无不包,細无不有其形狀。故天地為乾坤之象,乾坤為天地之用。天地尊卑既分,則乾坤之位因而可以制定也。然則首言天地尊卑者,蓋萬事之理、萬品之類,皆自乾坤為始,故先言天地尊卑也。
卑高以陳,貴賤位矣。
《義》曰:卑者謂地體卑下,高者謂天體高上。夫天地卑高既定,則人事萬物之情皆在其中,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各有貴賤高卑之位,是以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長幼皆有其分位矣。若卑不處卑,高不處高,上下錯亂,則貴賤、尊卑、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長幼不得其序,夫如是无高卑之分位矣。故此貴賤之分皆自高卑之位既陳,然後從而定矣。
動静有常,剛柔斷矣。
《義》曰:夫天以剛陽居於上則為動,地以柔隂居於下則為静。天地之道,生成萬物,各有常度。動而有常則為剛,静而有常則為柔。動静既有常分,生成各有常理,則剛柔可以斷矣。以人事言之,夫君以剛德居於上為動,臣以柔道居於下為静。君出其令而臣行之,臣納其善而君聽之。君臣動静既有常理,則剛柔之分可以斷矣。若動而不常,則剛道不成;静而不常,則柔道不立。夫如是,則剛柔不可以斷定也。然則此經雖論天地之性,然亦兼總萬物之動静也。
方以類聚,物以羣分,吉凶生矣。
《義》曰:此已下言聖人法天地之象也。方者,道也。天君子之人,同道而齊術。道同於已者,則相推而類聚之。君子則以君子為朋偶,小人則以小人為類黨,為士者則以士為同道,為濃者則以農為族黨,為工者則以工為同道,為商者則以商為類聚。是皆以同道為之共處,各隨其類族矣。物以羣分者,上既言君子小人各從其類,此又言萬品之物亦各以其羣類而為黨也。至如飛者則以飛者為羣,走者則以走者為羣,以至昆蟲、草木、巖穴之物,各從其羣,各從其分也。吉凶生矣者,夫上言方以類聚,物以羣分,此言吉凶生矣者,何哉?夫吉凶生於異類,善惡由夫影響。同逍齊術者則為吉,非其類者則為凶。若君子同於君子之人則吉,小人入於君子之黨則凶。是吉凶之道,生於非類,无所分别。若平其所趣,則凶是以生焉;若順其所同,則吉是以生焉。是吉凶之道,生於非類者也。
在天成象,在地成形,變化見矣。
《義》曰:象謂日月星辰也,形謂山川草木也。夫天以剛陽之氣居於上而生物,地以柔隂之氣在於下而承天。在於天者,則為日月星辰之象;在於地者,則為草木山川之形。是天地之道,生成之理,自然而然也。變化見矣者,上既言在天成象,在地成形,此復言變化見矣者,何哉?蓋天地之道,生成之理,有全體而化者,有久大而化者,有驟然而化者。千變萬化,皆有形象,而人莫能究其實,但知其自然而然也。
是故剛柔相摩,八卦相盪。
《義》曰:此已下明天地隂陽相推盪之事也。夫天本在上,地本在下,及夫天氣下降,地氣上騰,陽極則變而為隂,隂極則反而為陽,陽剛而隂柔,隂消而陽伏,剛柔互相切摩,更相變化,然後萬物之理得矣。夫八卦之始本於天地,剛柔二體法於隂陽,剛則為陽爻,柔則為隂位,爻位相錯雜,然後以成八卦推盪於天地之間。若十一月一陽生而推去一隂,五月一隂生而推去一陽,是八卦相推盪於天地之間,所以成於六十四卦也。
鼓之以雷霆,潤之以風雨。
《義》曰:鼓者,動也。雷者,隂陽二氣相激搏,則其聲為雷。霆者,怒雷則謂之霆。風所以生萬物,雨所以潤動植也。此至一寒一暑,重明上文變化見矣。及剛柔相摩,八卦相盪之事也。夫天地二氣相盪而成八卦之象,相推而成萬事之理。又鼓之以震雷離電,滋潤以巽風坎雨,使天下之物无不遂其性者,天地之道也。然而風亦言其潤者,蓋風者是生成之氣,能滋生於萬物,故亦言其潤也。
日月運行,一寒一暑。
《義》曰:日者太陽之精,月者太隂之精,寒者是純隂之氣,暑者是純陽之氣也。夫天地之道,生成萬物,既鼓動以雷霆,又滋潤以風雨,以日而煦育之,以月而照臨之。及夫日月運行,以成晝夜,以成寒暑之候,以盡生成之功者,天地之道也。然而直云震、巽、離、坎,不云乾、坤、艮、兌者,蓋乾、坤之道,上下備言,艮、兌非鼓動運行之體,故不言之。其實亦雷電風雨出於山澤,故亦兼包其義焉。
乾道成男,坤道成女。
《義》曰:道者,自然而生也。此言乾坤之道也。夫天以純陽在上,故為乾;地以純隂在下,故為坤。乾主乎剛健,坤主夫柔順。乾自然而為男,則為君、為父、為長、為上;坤自然而為女,則為臣、為子、為婦、為少。乾居於上則為尊,坤居於下則為卑。二氣交感,以生萬物,故有男女之象。然則坤必言成者,蓋乾因隂而得為男,坤因陽而得為女,故言成也。
乾知大始。
《義》曰:大始者,是隂陽始判,萬物未生之時也。乾者,天之用也。夫乾以天陽之氣在於上,故萬物莫不始其氣而生,莫不假其氣而成。得其生者,春英夏華,秋實冬藏。承其氣而成者,則胎生卵化,蠕飛動躍。是乾知大始起於无形,而入於有形也。
坤作成物。
《義》曰:坤者,是地之形也。物者,萬品之物也。夫地以純隂之氣在於下,上承於天陽之氣,以生萬物,无所不載,无所不育,是乾始於无形,而坤能載之,以作成萬物之形狀也。然乾言知,坤言作者,蓋乾之生物,起於无形,未有營作,坤能承於天氣已成之物,事可營為,故乾言知,而坤言作也。
乾以易知,坤以簡能。
《義》曰:夫乾之生物,本於一氣,其道簡略,不言而四時自行,不勞而萬物自遂,是自然而然者也。坤以簡能者,夫坤之生物,假天之氣,其道亦簡略,其用省默而已,不假煩勞而物自生,不假施為而物自遂,是自然而然者也。然則乾言易知,坤言簡能者,何也?蓋乾體在上,坤道在下,萬物始於无形,而乾能知其時,下降而生之。坤道在於下,而能承陽之氣,以作成萬物之形狀,其道凝静,不須煩勞,故乾言易知,坤言簡能也。若夫生成之道,於物艱難,則不為易知,若於事煩勞,則不為簡能也。
易則易知,簡則易從。
《義》曰:此復說上乾以易知也。夫天之道,寂然不見其用,杳然而不知其為,及夫四時之代謝,萬物之生殺,不待煩勞而自然者也。夫人君居兆民之上,為生靈之主,天下之事固不可以一言而盡也。然而必當法此乾道簡易之德,以總萬事之要目,則天下之道亦自然簡易而知也。簡則易從者,復解上坤以簡能也。夫地以純隂之氣,上承於天,以生萬物,不在煩勞而自然簡易,天下之物各遂其性者也。夫為臣之道,為國家之梁棟,作士民之冠冕,必當法此地道之簡易,承君之命,宣君之化,敷布於天下,簡其萬事之要,則天下可易從矣。
易知則有親,易從則有功。
《義》曰:此二句論聖賢法此乾坤簡易之理也。親者,親比也。言聖人法此天道,簡其萬事之要,不假繁冗,屑屑於治體,惟在廣其仁義生成之道,以及於天下,昭蘇萬有,養育萬民。夫如是,則天下之人皆悅而親比之也。易從則有功者,言人臣之道,法此地道,奉君之命,行君之事,不在繁冗,使天下之人於事易從,不在冗屑,而其功易成也。
有親則可久。
《義》曰:此二句論人法乾坤,久而益大也。物既和親,无相殘害,故可久也。言聖人既能法天之生物,順其萬物之情,成其至道之要,施之无窮,傳之萬世,天下之人既親比之,久而不朽,此聖人之道至大者也。
有功則可大。
《義》曰:事業有功,則積漸可大。此言為臣之道,既能法地之道,承事其君,以成其功業,至大至廣,使人易從。
可久則賢人之德。
《義》曰:夫天之所以覆而不知所以覆之義,地之所以載而不知所以載之理,浩浩然其神之所為者,天地之功也。聖人顯諸仁,藏諸用,若日月之照臨而不知照臨之迹者,聖人之功也。然聖人之操心積慮,法天地簡易之德以生養天下,使天下之人不可名狀以成其德也。
可大則賢人之業。
《義》曰:此言賢人之分,則見所為之迹也。夫為臣之道,既能法地之簡易,以成久大之功業,垂之萬世而不朽,此賢人之業也。然則此聖人言德,為臣者言業,何也?蓋聖人代天理物,法天行事,施其德澤,以滋生於天下,順其物情,以至昆蟲草木,皆蒙其澤,无所不燭,故其功不可以形狀,如天之无不覆,如地之无不載,故稱曰德。為臣之道,法地之理,以承君之命,行君之事,執其柔順之道,順從於人,以成其功,然出一令,行一事,皆稟君上之命,而可以形狀,故謂之業也。然此不言聖人,而言賢人者,何也?此聖人垂教之法也。言賢人亦可以法天之簡易而行事,以生成於天下,恐後世之人,止謂聖人可以法天之行事,故不言聖人,而言賢人也。且賢人尚可法之,則聖人固可知也。
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。
《義》曰:言聖人既能從其簡易,不在煩勞,發號施令,廣布德澤,以成天下之功,使天下之人,天下之物,長幼上下,尊卑貴賤,各得其分,如此則天下无為而治,聖人之理得矣。
天下之理得,而成位乎其中矣。
《義》曰:言聖人既能順其簡易之道,順其萬事之理,使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長幼各得其序,則天地之位皆由此矣。
聖人設卦觀象。
《義》曰:此已下至自天祐之為一章。上既言易之所起,始於乾坤,故首言天地之道。然天地始判,而萬物之情已在其間,故易之所始,因萬物之情而作,故曰易始於天地。此又言聖人設六十四卦之事。夫天地既判,而萬物之情已見於其間,是故聖人仰則觀象於天,俯則觀法於地,揆人事之理,盡萬物之情,乾坤水火風雷山澤之象,設為六十四卦,以通天地鬼神之情狀,以為萬世之法也。
繋辭焉而明吉凶。
《義》曰:六十四卦既設,其道至大,其理至深,聖人若不繋之以辭,散於諸爻之下,則後世之人不能曉聖人設卦之意也。然則卦爻之中有剛有柔,分隂分陽,隂陽相推盪於其間,則有凶有吉,有失有得,故六爻之下皆繋屬其辭,得其正者則其辭吉,失其處者則其辭凶。
剛柔相推而生變化。
《義》曰:此已下言天地人事之理也。夫天地既判,剛柔二氣互相推盪以生成萬物,有全體而化者,有漸而化者,有胎而生者,有卵而化者,千變萬化,自然而然,皆由剛柔之氣互相推盪以成變化也。如乾之初九交於坤之初六,其卦為震。
是故吉凶者,失得之象也。
《義》曰:此總明諸卦象不同之事也。夫吉凶生於非類,悔吝生於動静,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有剛有柔,有正有不正。若辭之吉者,是得之象也;辭之凶者,是失之象也。合於道而不失其正者為吉,不合於道悖於其理者為凶,是吉凶者失得之象也。然觀六十四卦之中,言吉凶者義有數等,或吉凶之事據文可知,或不須明言吉凶而吉凶自見。若乾之九五飛龍在天,尋文考義,是吉可知也,故不須云吉也。若剝之不利攸往、離之九四突如其來如、焚如、死如之屬,據其文辭,其凶可見,故不言凶也。亦有爻處吉凶之際,吉凶未定,行善則吉,行惡則凶。若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,夕惕若,厲无咎,若屯之六二屯如邅如,乘馬班如,匪寇婚媾,女子貞不字,十年乃字,是吉凶未定,故不言吉凶也。有直言吉者,若坤之六五黄裳元吉,以隂居尊,嫌其不吉,故直言其吉。有直言其凶者,若剝之初六剝牀以足,蔑貞凶,若有一卦之内或有一爻之中,得失相形,須言吉凶。若大過九三棟橈凶,九四棟隆吉,是一卦相形也。屯之九五屯其膏,小貞吉,大貞凶,是一爻相形也。亦有一事相形,終始有異,若訟卦有孚窒惕,中吉終凶。有有咎而能改之者,若豫之上六曰冥豫,成有渝,无咎,
悔吝者,憂虞之象也。
《義》曰:事之小小,己過其意,有可追悔者,曰悔。事之微小,可為鄙吝者,曰吝。夫人始於得失微小之事,雖不至於大咎,然亦當憂虞思慮之,不可謂之微小不思之。故事之小者,必至於大;惡之漸者,必至於著。惡積而不可掩,罪大而不可解者,皆自細微以成之也。故易中所言吉凶者,是得失之象;言悔吝者,是憂虞之象也。
變化者,進退之象也。
《義》曰:夫物之生,有全體而化者,有漸而變者,此皆是進退之象也。夫進退之象,有盛衰之理,生死之道,吉凶之驗,皆自於盛衰。故來則為盛,往則為衰。故六爻之中,有剛有柔,或從始而上進,或居終而倒退,往來不窮,互相推盪,以成進退之象也。若乾之上九言亢龍有悔,復之初九言不遠復,无祗悔,元吉。
剛柔者,晝夜之象也。
《義》曰:夫聖人設卦,分其剛柔,以明人事之要,以盡萬物之宜。剛則為陽,為明,為晝;柔則為隂,為幽,為夜。剛柔相推,以成晝夜幽明之理,變通之道,以成吉凶悔吝憂虞之象也,故總言之也。然推觀其上文,始總言繋辭焉,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,此又别言吉凶者失得之象,悔吝者憂虞之象,變化者進退之象,剛柔者晝夜之象者,何也?蓋吉凶悔吝失得晝夜之象,皆由剛柔相推盪而致者,故得失有重輕,變化有小大,合之則同,分之則異,故始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,不云晝夜者,是總變化而言也。上文云吉凶者失得之象,下文又云悔吝者憂虞之象者,蓋吉凶之事皆由得失而成,得失之本皆由悔吝而成,悔吝之本皆由憂虞而有也。
六爻之動,三極之道也。
此復明變化進退之義也。夫易卦之中,則有六爻,故下二爻以象地,中二爻以象人,上二爻以象天。是六爻之中,三才之道畢矣。然六爻之道,有變有動,有凶有吉,有得有失。若動而合于道則為吉,動而悖於事則為凶。是六爻之動,互相推盪,則是天、地、人三才窮極之事,故有吉凶、悔吝、得失、變化之道也。
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,易之序也。
自此已下,言君子觀聖人設卦作易之意,以為修身之法也。夫易卦之中,有凶有吉,有否有泰,有悔有吝,有變有化,有得有失,有剛有柔。夫君子之人,觀此剛柔、變化、吉凶、得失、悔吝、憂虞之象,知其易之以序,以修其身,以行其事,以之居處進退,不惟尊卑、貴賤、貧困之間,皆得以安止也。至如乾之初九言潛龍勿用,是言君子之人可隱則當隱也。九二則言見龍在田,是言君子之人可進則當進之。又如居泰之時,則君子可引類而進於朝;居否之世,則有否塞不通之象;居於家人,則行治家之法;居旅之時,則為行旅之事。如此之類,皆是用得其時,不失其道,不惟尊卑、貴賤、貧困、窮極、安處、進退之間,皆可行之,是易之序也。
所樂而玩者,爻之辭也。
《義》曰:夫君子之人,既能知易之以序,以為居處之術,又當樂玩其六爻之辭。夫六爻之辭,有凶有吉,有否有泰,有得有失,皆隨時而變通。是故君子之人,必當愛樂而躭玩之,見其善則思齊其事,見其惡則思懼而改,趣其治而去其亂,向其安而舍其危,以至吉凶之事,悔吝之道,至纖至悉,无不備於爻辭之間。故君子所樂而玩者,爻之辭也。
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,
《義》曰:夫爻卦之間,有凶有吉,有失有得。君子之人,故當居處之間,觀其設卦之象,明其萬事之理,以躭樂六爻之辭,以知事之吉凶,明其事之得失,以至死生之道,變通之理,則无咎過之事。
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。
《義》曰:夫易以變而為占,自六爻之中皆變而為占。故古者取其蓍草之數,隨其變而占之,以明休咎之事,以究鬼神之奥。故君子若觀此六爻之變,凡於動静興作之間,必知其休咎之驗矣。
是以自天祐之,吉无不利。
《義》曰:言君子之人,既能居則觀其辭,動則玩其占,以奉順易象,則身无有凶害。如此,則自上天之所祐助,鬼神之所協吉,何所不利也?
彖者,言乎象者也。
《義》曰:疏以為自此至死生之說為一章,則非也。今觀其文辭,當從辭也者各指其所之為一段,自易與天地凖而下至盛德大業為一章是也。彖者,言乎象者也。自此以下至辭也者各指其所之為一章。上章既言吉凶悔吝,聖人設卦繋辭之義,細意未盡。此復言文王作彖,分於諸卦之下,以釋一卦之義。雖然,有周公爻辭散於諸爻之下,然文王之彖,其義淵深,孔子復作彖辭以解之。彖者,總論一卦之象。如乾之彖,元亨利貞曰大哉乾元,坤元亨曰至哉坤元,屯元亨曰屯,剛柔始交而難生,蒙亨曰蒙,山下有險,是皆解一卦之辭也。故曰:象者,言乎其象也。
爻者,言乎變者也。
《義》曰:夫六爻之設,内外二體,有變有動,有凶有吉,各隨時而變改之。然文王之作彖辭,以釋一卦之象,然其義亦有未盡。周公復作爻辭,散於諸爻之下,總人事之要道,明萬事之吉凶,隨其爻而通變之,各順其用。
吉凶者,言乎其失得也。
《義》曰:夫爻象之設,有凶有吉,有剛有柔。若陽居陰位,則不得其正;或陰居陽位,則或失其常。或近而不相得,或遠而有所比。合於道者則吉,乖於道者則凶。故吉凶之端,失得之義,盡在於爻辭之間矣。上文吉凶者,失得之象也。
悔吝者,言乎其小疵也。
《義》曰:疵者,病也。夫人禍發於細微,姦生於隱暗,事有至小而可以追悔者,行有至微而可以鄙吝者,故當憂慮而戒慎之。夫小惡不改以至於大惡,小善不積以至於大凶,至乎鄙吝之道,皆由微小而生也。故君子之人,觀此爻象之辭,則知動静之理,積其小善以成於大善,積其小惡以至於大惡,捨其失而處其得,悖其凶而從其吉,故悔吝之來,皆由微小而至矣。
无咎者,善補過也。
《義》曰:夫人所以有咎者,蓋由操心積慮,過為其事,小惡不改,以成乎大惡,小過不防,以至乎大過,所以有咎。如噬嗑上九屨校滅趾之類是也。此言无咎者,蓋言人之有失者,善能自改之,故六爻之中,有能改過而无咎者。若豫之上六曰:冥豫,成有渝,无咎。隨之初九曰:官有渝,貞吉。從正則吉也。
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,
《義》曰:位者,即六爻之位。夫一卦之中,凡有六爻,分其上下,有尊有卑,有小有大。若九五則言君位,九三則言臣位,是尊卑大小各有其分,則貴賤之位從而定矣。
齊小大者存乎卦。
《義》曰:夫陽主剛明而有生成之德,故其德大;陰主柔順而有消剥之行,故其德小。故六十四卦皆本陰陽剛柔之理以定其位也。故有大有小,君子必當明辨之。至如乾之與坤,泰之與否,損之與益,小過與大過,既濟與未濟,是皆所用不同,有小有大,各隨時而用之也。
辨吉凶者存乎辭。
《義》曰:辭者,卦爻之下所繋之言辭也。夫六十四卦有陽居陽位,陰居陰位,有以陽居陰位者,有以陰居陽位者,有以臣居君位者,有以君居臣位者,如此之爻位多矣。聖人若不繋之辭,則凶吉无由見矣。至如比之六二,居得其正,則其辭曰:比之自内,貞吉。小畜之初九,以陽居陽,則其辭曰:復自道,何其咎,吉。隨之九四,以陽居隂,則其辭曰:隨有獲,貞凶。觀之初六,以隂居陽,則其辭曰:童觀,小人无咎,君子吝。噬嗑之上九,以陽居隂,曰:何校滅耳,凶。是吉凶之文,皆在於所繋之辭也。君子之人若明辨吉凶之事,觀其辭則可知矣。
憂悔吝者存乎介。
《義》曰:介者,纎介也。悔吝者,小疵病也。夫人小惡不改,以成於大惡;小疵不補,以成於大疵。勿謂小善无益而不為,勿謂小惡无傷而弗去。及夫惡積而不可揜,罪大而不可解,以至何校滅耳,喪身夷族,然後悔之,亦其晚矣。故聖人凡小疵病鄙吝之事,必先憂虞之,所以獲其无咎也。然則萬事之理,皆始自纖芥,故聖人豫防之。故坤卦曰履霜堅氷者,則聖人教人防微杜漸之深戒也。
震无咎者存乎悔。
《義》曰:震者動也,悔者過也。夫人所以舉動而无咎者,蓋有剛明之才,有至正之德,知其吉凶之道,明其得失之迹。事之小疵者,預憂虞之;事之將失者,心改悔之。所以舉動而无咎者,蓋存乎悔也。
是故卦有小大,辭有險易。
《義》曰:其道光明則謂之大,其道消散謂之小。夫六十四卦之設,有大有小,有通有塞,故六爻之中,有變有動,有險有易。若履得其正,居得其中,行事无過,則卦爻之下,亦有和易之辭。若履非其正,居非其位,行事失其中,則卦爻之下,亦有險難之文。至如居泰之時,則言君子道長;居否之時,則言君子道消;明夷之時,則言明有所傷;大壮之時,則言大者壮也。以至吉凶悔吝,善與不善,惡與不惡,卦爻之下,各繋其辭以明之,故上文所謂齊小大者存乎卦者是也。
辭也者,各指其所之。
《義》曰:言六十四卦所繋之辭,各指事而言也。至如適於泰卦則其辭和易,適於蹇卦則其辭艱險,適於謙卦則其辭巽順,適於離卦則其辭文明,是各指其事之所變而言也。
易與天地凖。
《義》曰:自此已下至鼔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,盛德大業至矣哉為一章。上既言卦爻辭理之義,此又廣明易道深遠,可以與天地相參凖也。夫天地之道,福善禍淫,善者則祐助之,惡者則傾覆之,以至生成萬品之物,皆以簡易之道自然而然也。夫易之道本始於天地,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,所以統三才而妙萬物也。故爻之善者則其辭善,爻之惡者則其辭惡,得其正者則其辭吉,失其正者則其辭凶,以至總包萬事之理,皆以簡易之道自然而然也。是大易之道之可以凖擬於天地也,至乾以健而法天,坤以順而法地之類是也。
故能彌綸天地之道。
《義》曰:彌者,縫也;綸者,經也。言易道微妙,包含萬象,知鬼神之情狀,明人事之終始,上可以彌縫補合於天道,下可以經綸牽合於地理,无所不載,无所不備者也。
仰以觀於天文,俯以察於地理。
《義》曰:天文者,則是日月星辰,布設懸象成文章,故稱文也。地理者,則謂山川原隰,高卑上下,各有條理,繁盛於地,故稱理也。夫易之本始,始於天地,聖人仰以觀於天文,俯以察於地理,揆萬物之情,盡人事之理,以至纎至悉,无所不包,无所不備,是易之道也。
是故知幽明之故,原始反終,故知死生之說。
《義》曰:幽者,无形之謂也;明者,有形之義也。明則為晝為陽,幽則為夜為隂。夫聖人之作易,本凖擬於天地,下總括於事物,鬼神之情狀,吉凶之萌兆,隂陽之運動,幽明之義理,莫不統包於其間矣。原始反終,故知死生之說者,夫易道深遠,知幽明之故,以原究事物之終始反復,天人之本末,萬物之榮枯,四時之變化,吉凶之兆,動静之理,以至死生之說,莫不知之。
精氣為物,遊魂為變。
《義》曰:精氣者,則為隂陽精靈之氣也,氤氲積聚而為萬物也。遊魂者,伸為物之積聚,歸為分散之時,則謂遊魂。夫天地之道,隂陽之精氣萃聚而生萬物。於萬物之間,受隂陽之精氣而靈者,則為人。人受隂陽之精氣萃之於身,則有耳、目、口、鼻、心知、髮膚,而為之體魄也。合於人身,則謂之魂。故口能言,目能視,耳能聽,心能思慮,則謂之神。故用思慮、心知、才能,則謂之變。得精氣之多者則為神,得精氣之少者則為魄。及夫思慮既久,精神已倦,心知已勞,髮膚漸衰,用之太過。及其死也,體魄降於地,骨肉斃於下。精神散之於天則為神,體魄散之於下則為鬼。是天地之精氣萃聚於人身,則為精神、體魄矣。故左氏載子產之言曰:心之精爽,是謂魂魄。魂魄去之,何以能久?是言凡人得精氣之多者為神,受精氣之少者為魄。神魄萃之於身,久而必去,則精氣歸於天,則為神。骨肉斃於下,散而无所之,則為鬼。又禮記祭
《義》曰:氣也者,神之盛也。魄也者,鬼之盛也。合鬼與神,教之至也。衆生必死,死必歸土,此之謂鬼。骨肉斃於下,隂於野土,其氣發揚於上,為昭明、焄蒿、悽愴,此百物之精也,神之著也。是言人之生則精氣聚而為神,死則骨肉散而為鬼。而精魂改變,去形離體,則為變化之道也。
是故知鬼神之情狀。
《義》曰:鬼神者,不疾而行,不言而信,視之弗見,聽之弗聞者,鬼神之道也。夫鬼神之道,本諸精氣體魄聚之而生,亦由骨肉體魄散之而有,冥冥然不知其所在。聖人以其為无,則曰不仁,以其為有,則曰不知,其有形狀可覩哉!然此言知其形狀者,蓋言易道至大,通於天地,達於幽明,不惟幽隱章顯之間,而易道可以見矣。
與天地相似,故不違。
《義》曰:此已下言易道廣大,盡生死之理,幽明之故也。夫天地之道,春生夏長,秋殺冬藏,包含萬彚,无小无大,高者下者,飛者走者,莫不生育之,故不可以一言而盡也。夫大易之道,陽剛隂柔,窮幽極遠,總括萬事,從无入有,至纎至悉,莫不總明之,故不可一言而盡也。推其本原,大易之道皆聖人窮神盡性而作也。上則凖擬於天地,下則包言于人物,前乎天地則其道不過,後乎天地則其道不異,中於天地之間則其道若合符契而无違越,是易之道與天地相似者也。
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,故不過。
《義》曰:聖人无物不知,是知周也;天下皆養,是道濟天下也;萬事皆得其宜,是不過也。夫聖人以仁知之德,才能思慮,周及萬物,至於纎介之類,皆蒙被之。又以仁義施及天下,使萬品之物,天下之人,皆得其所,皆獲其濟。而又所行之事,合於大中,无過无不及之事。
旁行而不流。
《義》曰:夫聖人中天下而立,正南面而居,拂其己之私邪,去其已之阿黨,所行之事,中立而不倚,正行而不邪,以天下為一家,以萬民為一情,凡所動作,莫不會合大中之道而行之。此言旁行而不流者,蓋言聖人非善於一身,以至正之德,上符於天,下合於地,中合於人,无私无枉,无所不契,雖旁行於天下之間,亦无私邪淫過流蕩之事。所以然者,蓋至公至正而致然也。
樂天知命,故不憂。
《義》曰:順天施化是樂天,識物始終是知命。夫聖人順天施化,識物始終,以其不可改者,天命也。由是推測天道,以知己命。至於富貴夀考,貧賤夭折,皆繋於天,是以心无憂恤。雖在貧賤,亦不為險詖之行;雖在富貴,不為奢侈之心。故孟子曰:莫之為而為者,天也;莫之致而至者,命也。是言人之性,命之理,死生之道,皆本於天,固无可奈何。然則富貴稟於天,死生繋乎命,既无可奈何,則宜順從於天道,樂天而知命,原始而思終,安静而居,則无憂恤也。
安土敦乎仁,故能愛。
《義》曰:安者,静也;愛者,養也。夫聖人稟天地之全性,五常之道皆出於中,天下有一物不被其賜者,若已内於溝壑。由是推己之性以觀天下之性,推己之仁以安天下之物,使天下之人、萬品之物皆安土而定居矣。人能安土,物既遂性,則父母、兄弟、親疎、上下逓相親睦,而敦仁愛之心矣。
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。
《義》曰:範謂模也,圍謂周也,過者違也。夫聖人粹天地之靈,中天地而立。觀天地之性,然後正己之性;觀天地之情,然後正己之情。凡所行事,皆模範於天地隂陽之端。至如樹木以時伐,禽獸以時殺,春夏則生育之,秋冬則肅殺之,使物遂其性,民安其所,是範圍天地之化而无過越也。
曲成萬物而不遺。
《義》曰:曲者,曲屈委細而成就萬物也。遺者,棄也。夫聖人宅天下之廣居,司萬物之性命,模範天地以施化,輔相天地以保民,雖事物之微,昆蟲之細,亦皆以仁信屈曲而成就之。至如綱罟以時,不麛不卵,是皆物之微細而不遺棄也。
通乎晝夜之道而知。
《義》曰:通者,无所不通之謂也。書則為明,為陽也;夜則為幽,為隂也。夫聖人得天之正性,秀出於人上,與天地合其德,與日月合其明,通曉隂陽之宜,默運鬼神之奥。雖晝夜之道,幽明之理,无所不知,无所不曉。至如寒暑之代謝,星晷之相旋,隂陽之晦明,風雨之凄暴,未有不先知之矣。自此已上,皆言神之所為,精氣為物,遊魂為變之事。聖人能極神盡慮,推幽測隱,无所不知也。
故神无方而易无體。
《義》曰:神者,隂陽不測,幽微不可以測度,故曰神。无方者,不見所處,運動不息,是无方也。易者,即周易也。无體者,唯變所適,往來不窮,是无體也。夫天地之道,妙用无門,鬼神之道,寂然无迹,春生夏長,藏往知來,故不可以方隅而論之。夫大易之道,總括天地,包含萬象,惟變所適,道无常用,既不可以象類索,又不可以形器求,是亦不可以定體而論之也。是大易之道,與天地之道相凖,如鬼神之妙用也。
一隂一陽之謂道。
《義》曰:道者,自然之謂也。以數言之,則謂之一;以體言之,則謂之无;以開物通務言之,則謂之通;以微妙不測言之,則謂之神;以應機變化,則謂之易;總五常言之,則謂之道也。上既言天地之神,大易之道,窮變盡神,妙用无方,不可以方隅形體而求之。此又言天地生成之道。夫獨陽不能自生,獨隂不能自成,是必隂陽相須,然後可以生成萬物。故於冬至之日,陽氣下施,散而為春夏,以生成萬物,以至洪者、纎者、高者、下者,皆遂其生,以盈滿於天地之間。然萬物既生,不可不成之,故於夏至之日,隂氣下施,散而為秋冬,以成就萬物,以至洪者、纎者、高者、下者,皆遂其性,以成就於天地之間。是一隂一陽,互相推盪,天覆而地載,日照而月臨,所以謂之道也。
繼之者善也。
《義》曰:夫天地之道,隂陽之功,生成萬物,千變萬化,以盈滿於天地之間,使高者得其高之分,卑者得其卑之理。聖人得天地之全性,繼天地生成之功,以仁愛天下之物,以義宜天下之衆,使居上者不陵於下,在下者不過其分,是聖人繼天養物之功,以為善行也。故乾卦曰:元者,善之長。是言天以一元之氣,為衆善之長,聖人繼其元善之功,以理於物也。
成之者性也。
《義》曰:性者,天所稟之性也。天地之性,寂然不動,不知所以然而然者,天地之性也。然而元善之氣,受之於人,皆有善性,至明而不昏,至正而不邪,至公而不私。聖人得天地之全性,純而不雜,剛而不暴,喜則與天下共喜,怒則與天下共怒,以仁愛天下之人,以義宜天下之物。繼天下之善性,以成就己之性;既成就己之性,又成就萬物之性;既成就萬物之性,則於天地之性可參矣。是能繼天地之善者,人之性也。
仁者見之謂之仁,知者見之謂之知。
《義》曰:夫聖人得天性之全,故五常之道无所不備;賢人得天性之偏,故五常之道多所不備。或厚於仁而薄於義,或厚於禮而薄於信,是五常之性,故不能如聖人之兼也。夫大易之道,卦於伏羲,重於文王,爻辭於周公,是三聖人垂萬世法則之書。其間寫天地水火風雷山澤之象,本凖擬於天地,統鬼神之妙用,惟變所適,量時制宜,故不可一義而求之也。若仁者見之,則知聖人之仁;知者見之,則知聖人之知,是各資其分而已矣。
百姓日用而不知,故君子之道鮮矣。
《義》曰:夫聖人得天地之正性,繼天地之行事,故无所不知,无所不明。賢人得天地之偏,又可以仰及於聖人之行事。然聖人之道至深至奥,賢人尚可以偏窺之。至於天下百姓常常之人,得天性之少者,故不可以明聖人所行之事。夫大易之道,載聖人之行事,包乾坤之生育,鬼神之妙用,人道之終始,无不備於其間。聖人體其用,成其功業,發見於天下,則天下之人咸戴而行之,莫知所以然而然也。然而聖人君子雖能體易道以為用,觀易道以施化,然能悟君子之道者亦鮮矣。
顯諸仁,藏諸用。
《義》曰:上言神之所為,此論易道之大,與神功不異也。顯諸仁者,言道之為體,顯見仁功,衣被萬物,是其顯也。藏諸用者,謂潛藏功用,不使物知,是藏諸用也。夫天地之道,乾剛坤柔,日臨月照,春生夏長,秋殺冬藏,使萬物緜緜而不絶者,天地生成之仁也,然不知天地生成之用也。夫聖人之道,恩涵澤浸,政漸仁煦,薄賦輕役,恤孤軫貧,使百姓安其土而不遷,勸其功而樂事者,聖人生成之仁也,然不知聖人生成之用也。夫大易之道,寂然不見其體,杳然不見其形,以之悅懌生民,功業萬世,施為德澤,則可以衣被萬物,是顯諸仁也。及夫推究原本,測度云為,不見其迹,是藏諸用也。是大易之與天地鬼神,无以異也。
鼔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。
《義》曰:夫天地之道,以時而生,以時而殺,雷霆以鼔動之,風雨以滋潤之,使萬物洪者、纎者、高者、下者,皆遂其性。或萬物之中有夭折、暴亡、凶荒、札瘥者,皆任自然之理,不能憂恤之。夫聖人代天牧民,繼天之善,以仁義之道生成於天下,物之夭折、暴亡、凶荒、札瘥者,常如己内於溝壑之中。是天地之道,但能鼔舞於萬物,而不能憂恤於萬物也。聖人能生成於萬物,又能憂恤於萬民也。惜乎聖人所不得者,天地之權也。故大易之道,載天地生成之理,而不能與聖人同憂也。老子曰天地之道,氣猶槖籥,以萬物為芻狗者,此也。
盛德大業至矣哉!
《義》曰:此已下至隂陽不測之謂神為一章,此是十翼之中第五章。今注疏之說,皆以謂顯諸仁、藏諸用而下至道義之門為一章。今觀顯諸仁、藏諸用、鼔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三句,皆言上文天地不測之事。故自此盛德已下至隂陽不測之謂神為一章,自夫易廣矣、大矣而下至易簡之善為一章。盛德大業至矣哉者,夫天地之道,无所不生,无所不育。以生成之功言之,其德至廣,而其功至大也。聖人法天之用,廣生成之道,萬物由之而通,政教由之而理。而又作工巧以便器用,立商賈以通有无。為之綱罟,則以畋以漁;為之耒耜,則以耘以耨。天下之人,至於昆蟲草木,无不被其賜者。是聖人充盛之德,廣大之業,至極矣哉!然必云盛德大業者,蓋施於行則為德,行於事則為業也。
富有之謂大業。
《義》曰:自此已下,覆說大業盛德,因廣明易與乾、坤之事。夫天之生物,盈滿於天地之間,則謂之富。聖人法天之行事,布其德澤,施其教化,竭天下之財用,聚天下之民物,以為之富有。富有天下,措當世於不拔,故謂之大業也。
日新之謂盛德。
《義》曰:夫天地之道,日往月來,隂極陽生,四時更變,寒暑相推,一日復一日,其德愈新,以至生成萬物,日日而盛大。聖人法此天地之道,增修其德,持循政教,適時之變,量事制宜,使其德日日盛大。
生生之謂易。
《義》曰:生生者,隂生陽,陽生隂也。天地之道,聖人之德,以富有言之,則謂之大業;以日新言之,則謂之盛德。而又生成之道,變化死生,生而復死,死而復生,使萬物緜緜而不絶者,天地聖人之德業也。夫大易之道,盡七九八六之數,寫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之象,總隂陽生殺之理,包人事萬物之宜,變而必通,終而復始,隨時之變,因事制宜,凖擬天地之間,則其功不異,是生生相續而不絶也。
成象之謂乾。
《義》曰:乾者,健也。夫天以一元之氣,仰而望之,其色蒼蒼然,下周於地,其狀如倚杵。南樞入地三十六度,北樞出地三十六度,一書一夜,凡行九十餘萬里。自古至今,未嘗有毫釐之差忒,亦未嘗有分毫之不及,以至生成萬物,皆以乾健而神其用,以成就萬物之形狀,非剛健之功,則不能如是也。故伏羲始畫乾卦,皆取健用為象也。
效法之謂坤。
《義》曰:坤者,順也。夫坤,地之道,承天之氣,而始終萬物无所不載,无所不生,皆效天而生育之。故伏羲畫坤之卦,亦皆取效坤順之義,而名曰坤。然則必言成象之謂乾,效法之謂坤者,蓋萬物之生,必由天道剛健,然後成其形象;地道柔順,必得陽氣,然後順其物理。以人事言之,乾則為君之象,坤則言臣之道。天下之事,非君不能立;庶政之設,非臣不能行也。
極數知來之謂占。
《義》曰:夫大易之道,總包天地,動賾鬼神,天下之事不言而自知,吉凶之道未萌而先見,皆聖人以蓍象之數,占其事物之理,逆知來事之意,考其行事之驗,以成其文也。故下文所謂將有為也,問焉而以言,其受命也如響,此之謂也。
通變之謂事。
《義》曰:夫暑往則寒來,陽生則隂伏,物之所以理,事之所以通,生而後滋,周而復始,皆自於變化之力也。故黄帝通其變,使民不倦,神而化之,使民宜之。易窮則變,變則通,通則久,是皆自通變之道,然後成天下之事也。
隂陽不測之謂神。
《義》曰:夫萬物之生,皆由天地隂陽之功以生成之。然生成之道,周而復始,極而復生,不言而信,不疾而行,以至變化之理,及究其生育之形,不可得而知也。
夫易,廣矣,大矣。
《義》曰:自此已下至易簡之善配至德為一章,此十翼之中第六章贊明大易之道至廣而至大也。夫易變化極於四達是廣矣,窮於上天是大矣,故下文云廣大配天地是也。
以言乎遠則不禦。
《義》曰:遠者,四遠之外而不禦止也。夫大易之道,至廣而至大,極天地之淵蘊,盡人事之終始。推於天下,則天下之事无不備;施之萬世,則萬世之事皆可知;窮於四遠,則四遠之處不能以禦也。
以言乎邇,則静而正。
《義》曰:邇,謂近也。夫邇近之地,目所可覩,耳所可聞,思慮之所可及之處也。故大易之道,雖於邇近之間,窮理盡性,耳目之所覩,思慮之所及,寂然不見其形,杳然不見其迹,雖邪僻之不能干。至於幽,至於静,默然而得其正者,大易之道也。
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。
《義》曰:言大。易之道至廣而至大,以言乎遐遠之間,則不可禦止;以言乎邇近之處,則其道静默;以言乎天地變化之道,則无所不備矣。
夫乾,其静也專。
《義》曰:乾者,天之用也。夫乾之體,至剛至健,一晝一夜,凡行九十餘萬里,其剛健之德也如此夫。然而生育之時,雖純隂用事,而坤道承陽之氣,以發生萬物。雖當純隂用事之時,而陽氣凝然静默,任其專一之道,以生於物也。
其動也直。
《義》曰:直,謂正直也。言乾之用,雖未生萬物之時,其静也專。及其陽氣下降於地,以生萬物,其運轉則四時不忒,寒暑无差,剛而得正。
是以大生焉。
《義》曰:言天地之道,以其專一至静之德,運動而不失其正,是以能大生於萬物也。
夫坤,其静也翕。
《義》曰:翕者,斂也。夫坤之道,凝然在下,承天陽之氣以生於萬物,當陽氣未降之時,則翕斂其氣,閉藏其用也。
其動也闢,是以廣生焉。
《義》曰:夫坤之道,凝然在下,翕斂其氣,閉藏其用而不動。及其陽氣下降之時,開闢其用,承陽之氣以生於物。是以其生育之道,至廣而无限極也。
廣大配天地。
《義》曰:此已下申明大易之道也。言大易之道至廣而至大,无所不包,无所不備,上可以配之於天,下可以周之於地,其道至深而至遠也。
變通配四時。
《義》曰:夫易之道,至幽至賾,惟變所適,生而不絶,周而復始。變通之道,无所常定,亦可以配於四時。至如乾坤之道,生殺之理,春則生之,生之不已,必夏長之,長之不已,必秋成之,成之不已,必冬幹之。是四時生殺,皆有其時而變通。易有變通之理,所以配於四時也。
隂陽之義配日月。
《義》曰:夫易之中有隂陽,猶乾坤之有日月。夫日者,是至陽之精,照於晝而為明;月者,是至隂之精,照於夜而為明。故大易之道,變通之理,有剛有柔,有隂有陽,猶乾坤之有日月,運其寒暑以成晝夜。
易簡之善配至德。
《義》曰:夫大易之道,包含萬象,至纎至悉,无所不載。然而其道簡易,不尚煩勞,可以配天地之至德也。
子曰:易其至矣乎!
《義》曰:此已下至成性存存,道義之門為一章,此贊美易道至大至廣也。
夫易,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。
《義》曰:夫大易之道,至廣而至極,上可以括天之高明,下可以包地之博厚。聖人用之,可以增崇其至德,廣大其功業也。
知崇禮卑。
《義》曰:夫萬物之理,萬事之原,不能出於聖人之知。然聖人之知,必由禮而修飾之。故知崇則如天之高,至貴而人莫能及;故禮卑如地之下,至微而人不能出。是至崇者不能及於知之高,至卑者不能出於禮之用也。
崇效天,卑法地。
《義》曰:言聖人之知崇而上效于天,禮卑而下法於地。知以幽遠為上,則為崇;禮以卑退為本,故為卑也。
天地設位,而易行乎其中矣。
《義》曰:夫天以純陽之氣積於上,地以柔隂之氣積於下,天地初判,二位既設,則大易之位,萬物之情,以行於天地之間矣。
成性存存,道義之門。
《義》曰:性者,天所稟之性也。存存者,不絶之貌也。夫人稟天地之善性,至明而不昏,至正而不邪,至公而不私。若能觀天之性,而成就己之性,則可以生成於天下,以盡萬物之性,使萬物之性存存而不絶,而道義之門自此塗而出也。若夫不能觀天之性,以正己之性,則䧟於邪佞,而放僻之事從而至矣。如是,則不能成其道義之門,不能開通其物。故此大易之道,凖擬於天地,至公至正,无私无曲,成其治性之道,存存而不絶,成其道義之門,為人之所出入而取法也。
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,而擬諸其形容,象其物宜。
《義》曰:自此已下至負且乘,致寇至盗之招也為一章,注以謂至其臭如蘭,則非也。上既言易道變化,神理不測,此又明聖人見天下之賾,以成萬物之形象也。賾者,幽賾也,人之難見者也。言聖人推測天下之幽賾,以擬度萬事之理,以凖擬萬物之形容,以象萬物之所宜,使皆各得其宜,各順其性。至如剛之理則擬乾之形容,柔之理則擬坤之形容,艮之性則言其止,震之性則言其動,陽物則言其剛,隂物則言其柔,若泰卦則言泰之形容,象其泰之物宜,若否卦則言否之形容,象其否之物宜,其六十四卦之中,皆有所象矣。
是故謂之象。
《義》曰:此已上結成卦象之義也。夫言聖人因擬度萬物之形容,以象萬物之所宜,是故謂之象。象者,即文王所作彖辭,以明一卦之象也,則謂之象。然六十四卦之中,皆謂之象,故前章云:卦者,言乎其象也。是言聖人因推測天下之理,以明萬物之宜,故謂之象也。
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,而觀其會通,以行其典禮。
《義》曰:動,謂變動也。會,合也。通,謂通變也。言聖人觀此諸卦爻之變動,明其吉凶得失之要,以觀天地萬物會合變通之事。其有合於理,通於道者,則為之常禮而行之。其有悖於理,違於道者,則舍而去之。是聖人明六十四卦動静之理,變通之事,會合其典禮者也。
繋辭焉以斷其吉凶,是故謂之爻。
《義》曰:夫六十四卦,有剛有柔,有變有動,會合於典禮者則為吉,不會合於典禮者則為凶。然而其義幽微,常常之人不能明曉耳。是以聖人於諸卦諸爻之下,各繋屬其文辭以解釋之。若陽居隂位,則言其吉;若隂居陽位,則言其凶。或近而相得,則言其吉;或遠而不相比,則言其凶。或居泰之時,而行君子之事則吉;或居夬之時,而行剛壮之道則凶。是皆觀天下之變動,合剛柔之常理,而繋屬其辭,以斷定其吉凶之效也。是故謂之爻。爻者,效也。效諸物之變動,明萬事之常理。得其正者為吉,失其位者為凶。是吉凶之效,自爻之動静而見也。故上章云:爻者,言乎變者也。
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。
《義》曰:此覆說上文聖人見天下之賾也。夫小人之性,為讒為諂,常有害君子之心。然君子之人,凡所作事,使小人不得間而窺,不得伺而疑,故所行之事,坦然而行,小人不能以惡忌也。故大易之道,廣之如地,高之如天,君子小人之道,无不備載於其間。然雖有黜小人之辭,然无心專在於小人,但人事得失,皆備言之。故雖小人之心,亦不能惡大易之道也。
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。
《義》曰:此覆說上文聖人見天下之動也。夫天下之動,吉凶是非,姦邪情偽,莫不錯雜於其間。既姦邪情偽錯雜於其間,則天下從而亂矣。今此大易之道,亦无心於聖人。惟天地之通變,人事之終始,有會合於典禮者則為吉,悖亂於常道者則為凶,其文皆散在諸爻之下,以明變動之理。雖小人之情偽,亦不能錯雜而紛亂之。
擬之而後言,議之而後動,擬議以成其變化。
《義》曰:擬之而後言者,此覆說上文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。議之而後動者,此覆說上文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。言聖人觀天下之運動,明人事之得失,一言之出,必深思遠慮,然後行之。何哉?蓋言之有善有不善,若擬而出之,則其言必善;若不擬而出之,則其言或有不善;必須擬而出之,則言滿天下无口過。故云:夫人動静之間,亦須合於道。若議論而動之,則无悔吝矣;若不議論而動之,則悔吝有時而至焉;若議而動之,雖行滿天下,亦无怨惡也。若能言動之間,擬之而後為,議之而後行,則深思遠慮,久而必精,則可以通天下之變化,為天下之法則者也。
鳴鶴在隂,其子和之。我有好爵,吾與爾靡之。
《義》曰:上既言擬議於善則善應之,擬議於惡則惡應之,是猶鳴鶴之在隂,其同類者必相應之也。夫鳴鶴在隂者,此中孚之卦、九二之爻辭也。夫中孚之九二,上應於九五,當中孚之時,二五以至誠相應,用心不私,然雖為六三、六四以隂柔間厠於其間,進無所適,退无所遇,二五雖不得相會,然至誠相待,終得其應,此中孚之時卦象之如此也。是猶鳴鶴之在幽隂之中,而聲聞於外,其子從而和之也。我有好爵,吾與爾靡之者,亦是言至誠相待之故也。夫美好之爵不自獨有,宜與爾同類之人共分而靡之,是言結之深,用心不私,至公至正也。然此引而證之者,蓋明聖人之言行當擬議而行之,言之善者則善者應之,言之惡者則惡者應之,
子曰:君子居其室,出其言善,則千里之外應之,況其邇者乎?
《義》曰:此孔子因言聖人之言,出於其近以行於遠,出於其内以及於外,出於其身以行於人也。故君子之人,凡居其室,出一善言,可以為天下之法,可以興天下之利,雖千里之遠,而人皆從之,況於邇近之人乎?
居其室,出其言不善,則千里之外違之,況其邇者乎?
《義》曰:言君子之人,凡居其室,出一言不善,則不可為天下之法,不能除天下之害,不能興天下之利,則千里之人皆違而不從之,況邇近乎?
言出乎身,加乎民;行發乎邇,見乎遠。言行,君子之樞機。
《義》曰:樞者,戶樞,司其通塞之道;機者,弩牙,主其矢之中否也。夫言戶樞之發,或明或暗,主其通塞之道;弩牙之發,或中或否,主其發矢之中。猶君子之人,言行有善有不善者也。夫君子之言行,出之於身,行之於外,自邇而及遠,由中而及外。若發而為善,則天下從而法則之;若發而不善,則天下從而違去之。是言行之出,為命為令,有得有失。若尸樞之主通塞,猶弩牙之有中否,中則為天下之榮,否則為天下之辱。是言行者,君子之樞機也。
樞機之發,榮辱之主也。
《義》曰:言行者,本由君子之出發之,中與不中,是榮辱之主也。
言行,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,可不慎乎!
《義》曰:夫君子之言行,有善有不善,必當思慮之。若思之不精,慮之不深,則言之不善矣。善與不善,皆動之於天地也。故書曰:天聰明自我民聰明,天明威自我民明威。言天體雖高,而下聼於卑矣。夫君子之言善,則為號令,以除天下之害,以興天下之利,天下之人和樂而從之。民既和之,則善聲動於天。善聲動於天,則上天降其福。若言之不善,不能興天下之利,不能除天下之害,則天下之人嗟怨而不從之。天下之人既嗟怨而不從之,則怨氣瀆於天。怨氣瀆於天,則上天降之以禍。是君子之言行,出則動乎天地,必當精心而致思之,可不戒慎乎?
同人,先號咷而後笑。
《義》曰:此是同人九五之辭,言同人之九五下應於六二,然有九三、九四為己之寇難,六二以至誠相待,雖為三四寇難,終得為正應也。然此引之者,凡易之辭有理義未盡者,孔子復引而明之,言同人之九五始為三四寇難,不得與二為應,是先號咷也。然二五至誠相應,終得會遇,是後笑也。故因此言行,陳其至誠之道,故引以為義也。
子曰:君子之道,或出或處。
《義》曰:夫君子之人,懷才抱道,有經邦濟世之才。若遇其時,遇其君,則進登王者之朝,以濟天下之民,故曰或出。若不遭其時,不遇其君,則守其至正之道,待時而動,故曰或處。
或默或語。
《義》曰:夫君子之人,凡居於室,不可以妄語,但寂然不言,默然不語。或當可言之時,必精思而慎慮之,然後可言也。夫如是,雖言滿天下无口過,行滿天下无怨惡,使天下之人莫不悦而從之,而其心一歸於大中之道也。然則君子之人,同類相應,同心相得,不必同其道然後言之。至如禹、稷事於堯朝,憂天下之饑如己之饑,憂天下之溺如己之溺。又顔子一簞食,一瓢飲,在陋巷,人不堪其憂,孟子謂禹、稷、顔回同道。又如箕子佯狂殷紂,微子去之,比干諫而死,是皆其心異而其道同也。惟君子之言,必當擬而後言,議而後動,則語默出處,自然合於道矣。
二人同心,其利斷金。
《義》曰:金者,至堅之物也。夫君子之人,推誠以待物,則物以至誠待於己。凡是同心同類之人,皆感悅而從之,不必求同於己之道者,但其心一同則可也。至如二人同心,合謀共慮,成天下之能事,雖至纎至悉之利,亦可以斷截堅剛之金,是同心之人至利者也。
同心之言,其臭如蘭。
《義》曰:臭者,香氣也。蘭者,香草也。言君子之人,既能同心同德,合謀共慮,吐言發語,有馨香之臭氣,如芝蘭之馥郁芬芳,以達於天地之間也。
初六,藉用白茅,无咎。子曰:苟錯諸地而可矣,藉之用茅,何咎之有?慎之至也。
《義》曰:自此已下,當連上文為一章。注疏以此為第七章之始,非也。當連上文則是。此是大過初六之爻辭也。夫大過之時,政教陵遲,紀綱廢墜,上下失道,本末衰弱,惟是有大才德之人,過越常分以拯救之。然聖賢之人,雖過越常分以拯救天下之事,然居事之始,不可不慎重之。苟不能慎重之,則害於成事,而以災其身。夫置器於地,必安全而无傾覆之事。今置器於地,又以潔白之茅薦藉之,是過慎之至也。既過慎之,則安全而无傾覆也。故孔子因論君子擬議其言行,故以此明慎事之始。如置器於地,又藉以白茅,是慎之至也,何咎之有乎?
夫茅之為物薄,而用可重也。慎斯術也以往,其无所失矣。
《義》曰:夫茅之為物,雖柔弱菲薄,然祭祀之時,必取而為用,以薦藉宗廟之靈。雖為物甚微,然有潔白柔順之質,其用也重矣。聖人因其慎事之始,又取茅之所用之重,以明慎重之術。以此而往,則无所失。且天過之事,尚且如此,况於小小之事乎?
勞謙,君子有終,吉。
《義》曰:此是謙卦九三之爻辭也。夫謙之九三,以陽居陽,在下卦之上。以位言之,則居得其正;以身言之,則在人臣之極位。上奉於君,下在百官之上,其責至重,其職非輕。是以上則勞謙以事於君,下則勞謙以接於人,不以勤勞為慮,常惟曠官之責。夫如是,是勞謙君子有終者也。然則必言君子之終者,何也?夫小人之性,亦有謙順之時,然其心易變,朝行而夕改,不能終始而行之。唯其君子之人,慎始至終,有其本末,故云君子終吉也。在古之時,惟周公可以當也。夫周公是文王之子,武王之弟,成王之叔。當周之時,而相武王伐紂,一戎衣而天下定。迨夫成王幼弱,己居三公之責,攝天子之位,握天下之重權。位非不尊也,權非不重也,天下非不歸也,而周公盡人臣之忠節,竭人臣之思慮,以事於冲君,復制禮作樂,朝諸侯於明堂,天下臣民陶然而歸之。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