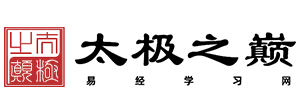【周易下经】第64卦-未济䷿火水未济(坎下离上)-[清]李光地《御纂周易折中•卷第八》

程传:《未济·序卦》:“物不可穷也,故受之以《未济》,终焉,”《既济》矣,物之穷也。物穷而不变,则无不已之理。《易》者,变易而不穷也,故《既济》之后,受之以《未济》而终焉。未济则未穷也,未穷则有生生之义,为卦离上坎下,火在水上,不相为用,故为《未济》。
未济,亨,小狐汔济,濡其尾,无攸利。
本义:“未济”,事未成之时也。水火不交,不相为用。封之六爻,皆失其位,故为《未济》,“汔”,几也。几济而濡尾,犹未济也。占者如此,何所利哉!
程传:《未济》之时,有亨之理,而卦才复有致亨之道。惟在慎处,狐能度永,濡尾则不能济。其老者多疑畏,故履冰而听,惧其陷也。小者则未能畏慎,故勇于济,“汔”,当为仡,壮勇之状。《书》曰:仡仡勇夫,小狐果于济,则“儒其尾”而不能济也。《未济》之时,求济之道,当致惧则能“亨”。若如小狐之果,则不能济也。既不能济,无所利矣。
集说:胡氏炳文曰:天地不交为《否》,《否》不曰“亨”,《否》不通也。水火不交为《未济》,非不济也,未焉尔,故曰“《未济》亨”。
案:“小狐”当从《程传》之解,“汔济”当从《本义》之解。要之是戒人敬慎之意,自始济以至于将济,不可一息而忘敬慎也。
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八:未济初六
初六,濡其尾,吝。
本义:以阴居下,当《未济》之初,未能自进,故其象占如此。
程传:六以阴柔在下,处险而应四,处险则不安其居,有应则志行于上。然己既阴柔,而四非中正之才,不能援之以济也。兽之济水,必揭其尾,尾濡则不能济。“濡其尾”,言不能济也。不度其才力而进,终不能济,可羞吝也。
集说:张氏振渊曰:卦辞所谓“小狐”,正指此爻。新进喜事,急于求济,而反不能济,可吝,孰甚焉。
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八:未济九二
九二,曳其轮,贞吉。
本义:以九二应六五,而居柔得中,为能自止而不进,得为下之正也,故其象占如此。
程传:在他卦九居二为居柔得中,无过刚之义也。于《未济》圣人深取卦象以为戒,明事上恭颐之道。《未济》者,君道艰难之时也。五以柔处君位,而二乃刚阳之才,而居相应之地,当用者也。刚有陵柔之义,水有胜火之象。方艰难之时,所赖者才臣耳。尤当尽恭顺之道,故戒“曳其轮”,则得正而“吉”也。倒“曳其轮”,杀其势,缓其进,戒用刚之过也。刚过则好犯上而顺不足,唐之郭子仪李晟,当艰危未济之时,能极其恭顺,所以为得正而能保其终吉也。于六五则言其“贞吉”光辉,尽君道之善。于九二则戒其恭顺,尽臣道之正,尽上下之道也。
集说:潘氏梦旂曰:九二刚中,力足以济者也。然身在坎中,未可以大用。故曳其车轮,不敢轻进,待时而动,乃为吉也。不量时度力,而勇于赴难,适以败事矣。
案:《既济》之时,初二两爻,犹未敢轻济,况《未济》乎,故此爻曳轮之戒,与《既济》同。而差一位者,时不同也。观此初二两爻,“濡其尾”则“吝”,而“曳其轮”则“吉”,可知《既济》之初,所谓“濡其尾”者,非自止不进之谓也。
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八:未济六三
六三,未济,征凶,利涉大川。
本义:阴柔不中正,居《未济》之时,以“征”则“凶”。然以柔乘刚,将出乎坎,有“利涉”之象,故其占如此。盖行者可以水浮,而不可以陆走也,或疑利字上当有不字。
程传:《未济》“征凶”,谓居险无出险之用,而行则凶也,必出险而后可证。三以阴柔不中正之才而居险,不足以济,未有可济之道出险之用,而征所以凶也,然《未既》有可济之道,险终有出险之理,上有刚阳之应,若能涉险而往从之,则济矣,故“利涉大川”也。然三之阴柔,岂能出险而往,非时不可,才不能也。
集说:赵氏汝楳曰:三居《未济》之终,过此则近于济矣,故特表以卦名也。
胡氏炳文曰:六三居坎上,可以出险,阴柔非能济者,故明言“未济征凶”。
案:此爻之义,最为难明。盖上下卦之交,有济之义,《既济》之三,刚也,故能济。《未济》之三,柔也,故未能济。《传》曰:“其柔危,其刚胜邪!”于此两爻见之矣。又《既济》、《未济》两卦爻辞,未有举卦名者,独此爻曰“未济”。盖他爻之既济未济者时也,顺时以处之而已。此爻时可济矣,而未能济,是未济在己而不在时,故言未济,见其失时也。无济之才,故于征则凶。有畏慎之心,故于“涉大川”则利,盖涉大川不可以轻进,未济无伤也,圣人之戒失时,而又欲人审于赴时也如此。
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八:未济九四
九四,贞吉,悔亡,震用伐鬼方,三年有赏于大国。
本义:以九居四,不正而有“悔”也。能勉而贞,则“悔亡”矣。然以不贞之资,欲勉而贞,非极其阳刚用力之久不能也,故为“伐鬼方”三年而受赏之象。
程传:九四阳刚,居大臣之位,上有虚中明顺之主。又已出于险,《未济》已过中矣,有可济之道也。济天下之艰难,非刚健之才不能也,九虽阳而居四,故戒以贞固则吉而“悔亡”。不贞则不能济,有悔者也。“震”,动之极也。古之人用力之甚者,“伐鬼方”也。故以为义。力勤而远伐,至于三年,然后成功,而行大国之赏,必如是乃能济也。济天下之道,当贞固如是。四居柔,故设此戒。
集说:俞氏琰曰:“震用伐鬼方”者,震动而使之惊畏也,《诗·时迈》云,“薄言震之,莫不震叠”,与此震同。
案:此“伐鬼方”,亦与《既济》同,而差一位也。“三年克之”,是已克也。“震用伐鬼”,是方伐也。“三年有赏于大国”,言三年之间,赏劳师旅者不绝,非谓事定而论赏也。与《师》之“王三锡命”同,不与《师》之“大君有命”同。
又案:三四非君位,而以高宗之事言者,盖《易》中有论时者,则不论其位。如《泰》之论平陂之运,而利于艰贞。《革》之论变革之道,而宜于改命。皆以上下卦之交时义论之也。
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八:未济六五
六五,贞吉,无悔,君子之光,有孚,吉。
本义:以六居五,亦非正也。然文明之主,居中应刚,虚心以求下之助,故得“贞”而“吉”且“无悔”。又有光辉之盛,信实而不妄,吉而又吉也。
程传:五文明之主,居刚而应刚,其处得中,虚其心而阳为之辅,虽以柔居尊,处之至正至善,无不足也。既得贞正,故“吉”而“无悔”。贞其固有,非戒也。以此而挤,无不济也。五文明之主,故称其光。君子德辉之盛,而功实称之,“有孚”也。上云吉,以贞也。柔而能贞,德之吉也。下云吉,以功也。既“光”而“有孚”,时可济也。
集说:杨氏万里曰:六五逢未济之世而光辉,何也?日之在夏,曀之益热,火之在夜,宿之弥炽。六五变未济为既济,文明之盛,又何疑焉?
案:《易》卦有“悔亡”“无悔”者,必先“悔亡”而后“无悔”。盖无悔之义,进于悔亡也。其四五两爻相连言之者,则《咸》、《大壮》及此卦是也。此卦自下卦而上卦,事已过中,向乎济之时也。以高宗论之,四其奋伐荆楚之时,而五其嘉靖殷邦之侯乎。凡自晦而明,自剥而生,自乱而治者,其光辉必倍于常时。观之雨后之日光,焚余之山色,可见矣。
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八:未济上九
上九,有孚于饮酒,无咎,濡其首,有孚,失是。
本义:以刚明居《未济》之极,时将可以有为,而自信自养以俟命,“无咎”之道也。若纵而不反,如狐之涉水而“濡其首”,则过于自信而失其义矣。
程传:九以刚在上,刚之极也。居月之上,明之极也。刚极而能明,则不为躁而为决。明能烛理,刚能断义。居《未济》之极,非得济之位,无可济之理,则当乐天顺命而已。若《否》终则有倾,时之变也。《未济》则无极而自济之理,故止为《未济》之极,至诚安于义命而自乐,则可“无咎”。“饮酒”,自乐也。不乐其处,则忿躁陨获,入于凶咎矣。若从乐而耽肆过礼,至“濡其首”,亦非能安其处也。“有孚”,自信于中也。“失是”,失其宜也。如是则于有孚为失也。人之处患难,知其无可奈何,而放意不反者,岂安于义命者哉!
集说:刘氏牧曰:《既济》以柔居上,止则乱也,故“濡其首厉”。《未济》以刚居上,穷则通矣,故“有孚于饮酒,无咎”。
石氏介曰:上九以刚明之德,是内“有孚”也。在《未济》之终,终又反于《既济》,故得饮酒自乐。若乐而不知节,复“濡其首”,则虽“有孚”,必失于此,此戒之之辞也。
邱氏富国曰:既言“饮酒”之“无咎”,复言饮酒濡首之失,何耶!盖饮酒可也,耽饮而至于濡首,则昔之“有孚”者,今失于是矣。
李氏简曰:《未济》之终,甫及《既济》,而复以濡首戒之。惧以终始,其要无咎,此之谓《易》之道也。
总论:郑氏汝谐曰:《既济》“初吉终乱”,《未济》则初乱终吉,以卦之体言之,《既济》则出明而之险,《未济》则出险而之明。以卦之义言之,济于始者必乱于终,乱于始者必济于终,天之道物之理固然也。
邱氏富国曰:内三爻,坎险也。初言濡尾之吝,二言曳轮之贞,三有征凶位不当之戒,皆未济之事也。外三爻,离明也。四言“伐鬼方”有赏,五言“君子之光有孚”,上言“饮酒无咎”,则未济为既济矣。
万氏善曰:《泰》之变为《既济》,《否》之变为《未济》,盖《既济》自《泰》而趋《否》者也,《未济》自《否》而趋《泰》者也。故《既济》爻辞无吉者,以其趋于《否》也。《未济》爻辞多吉,以其趋于《泰》也。《否》《泰》者,治乱对待之理。《既济》、《未济》者,《否》《泰》变更之渐也。
吴氏曰慎曰:《易》之为义,不易也。交易也,变易也。乾坤之纯,不易者也。《既济》《未济》,交易变易者也。以是始终,《易》之大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