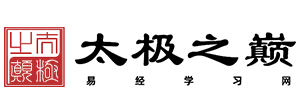[清]李光地《御纂周易折中•卷首》纲领二
御纂周易折中卷首:纲领二
此篇论易道精媪、经传义例
司马氏迁曰:《易》本隐以之显,《春秋》推见至隐。
班氏固曰:六艺之文,《乐》以和神,《诗》以正言,《礼》以明体,《书》以广听,《春秋》以断事。五者盖五常之道,相须而备,而《易》为之原,故曰“《易》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”。言与天地为终始也。
王氏弼曰:夫《彖》者何也?统论一卦之体,明其所由之主者也。故六爻相错,可举一以明也。刚柔相乘,可立主以定也。自统而寻之,物虽众,则知可以执一御也。由本以观之,义虽博,则知可以一名举也。故举卦之名,义有主矣。“观其彖辞,则思过半矣”。一卦五阳而一阴,则一阴为之主。五阴而一阳,则一阳为之主。夫阴之所求者阳也,阳之所求者阴也。阳苟一焉,五阴何得不同而归之?阴苟只焉,五阳何得不同而从之?故阴爻虽贱,而为一卦之主者,处其至少之地也。或有遗爻而举二体者,卦体不由乎爻也。繁而不优乱,变而不忧感,约以存博,简以济众,其唯《彖》乎!
夫爻者何也?言乎变者也。变者何也?情伪之所为也。是故“情伪相感”,远近相追,“爱恶相攻”,屈伸相推。“非天下之至变,其孰能与于此哉!”是故卦以存时,爻以示变。
夫卦者时也,爻者适时之变者也。时有否泰,故用有行藏。卦有小大,故辞有险易。一时之制,可反而用也。一时之吉,可反而凶也。故卦以反对,而爻亦皆变。寻名以观其吉凶,举时以观其动静,则一体之变,由斯见矣。夫应者,同志之象也;位者,爻所处之象也;承、乘者,逆顺之象也;远近者,险易之象也;内外者,出处之象也;初上者,终始之象也。故观变动者存乎应,察安危者存乎位,辨逆顺者存乎承、乘,明出处者存乎内外。远近终始,各存其会;辟险尚远,趣时贵近。比、复好先,乾、壮恶首。吉凶有时,不可犯也。动静有适,不可过也。犯时之忌,罪不在大。失其所适,过不在深。现爻思变,变斯尽矣。
夫象者,出意者也;言者,明象者也。尽意莫若象,尽象莫若言。言生于象,故可寻言以现象。象生于意,故可寻象以观意。意以象尽,象以言著。故言者所以明象,得象而忘言。象者所以存意,得意而忘象。存言者,非得象者也;存象者,非得意者也。象生于意而存象焉,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。言生于象而存言焉,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。然则忘象者,乃得意者也;忘言者,乃得象者也。爻苟合顺,何必坤乃为牛?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?而或者定马于乾,案文责卦,有马无乾,则伪说滋漫,难可纪矣。互体不足,遂及卦变。变又不足,推致五行。一失其原,巧喻弥甚。纵复或值,义无所取。盖存象忘意之由也。忘象以求其意,义斯见矣。
按象无初上得位失位之文,又《系辞》但论三五、二四同功异位,亦不及初上,何乎?唯《乾》上九《文言》云“贵而五位”,《需》上六云“虽不当位”。若以上为阴位邪?则《需》上六不得云“不当位”也。若以上为阳位邪?则乾上九不得云“贵而无位”也。阴阳处之,皆云非位,而初亦不说当位失位也。然则初上者,是事之终始,无阴阳定位也。故乾初谓之“潜”,过五谓之“无位”,未有处其位而云“潜”,有位而云“无”者也。历观众卦,尽亦如之。初上无阴阳定位,亦以明矣。位者,列贵贱之地,待才用之宅也。爻者,守位分之任,应贵贱之序者也。位有尊卑,爻有阴阳。尊者阳之所处,卑者阴之所履也。故以尊为阳位,卑为阴位。去初上而论位分,则三五各在一卦之上亦何得不谓之阳位?二四各在一卦之下,亦何得不谓之阴位?初上者,体之终始,事之先后也。故位无常分,事无常所,非可以阴阳定也。尊卑有常序,终始无常主,故《系辞》但论四爻功位之通例,而不及初上之定位也。然事不可无终始,卦不可无六爻,初上虽无阴阳本位,是终始之地也。统而论之,爻之所处则谓之位。卦以六爻为成,则不得不谓之六位时成也。
凡《彖》者,统论一卦之体者也。《象》者,各辩一爻之义者也。故《履》卦六三为兑之主,以应于乾;成卦之体,在斯一爻。故《彖》叙其应,虽危而亨也。《象》则各言六爻之义,明其吉凶之行。去六三成卦之体,而指说一爻之德,故危不获亨而见咥也。《讼》之九二,亦同斯义。一卦之体,必由一爻为主,则指明一爻之美,以统一卦之义,《大有》之类是也。卦体不由乎一爻,则全以二体之义明之,《丰》卦之类是也。
薛收问一卦六爻之义,王氏通曰:卦也者,著天下之时也。爻也者,效天下之动也。趋时有六动焉,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。收曰:敢问六爻之义。曰:六者非它也,三才之道?谁能过乎?
孔氏颖达曰:《易》者,变化之总名,改换之殊称。自天地开辟,阴阳运行,寒暑迭来,日月更出,孚萠庶类,亭毒群品,新新不停,生生相续,莫非资变化之力,换代之功。然变化运行,在阴阳二气,故圣人初画八卦,设刚柔两画,象二气也。布以三位,象三才也。谓之为《易》,取变化之义。郑康成作《易赞》及《易论》云:《易》一名而含三义,易简,一也;变易,二也;不易,三也。崔觐、刘贞简等并用此义。云易者谓生生之德,有义简之义。不易者,言天地定位,不可相易。变易者,谓生生之道变而相续。周简子云:不易者,常体之名;变易者,相变改之名。故今之所用,同郑康成等。作《易》所以垂教者,孔子曰:上古之时,人民无别,群物未殊,未有衣食器用之利,伏牺乃仰观象于天,俯观法于地,中观万物之宜,于是始作八卦,“以通神明之德,以类万物之情”。故《易》者,所以断天地,理人伦,而明王道,是以画八卦。建五气,以立五常之行。象法乾坤,顺阴阳,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。度时制宜,作为“罔罟”“以佃以渔”,以赡民用,于是人民乃治,君亲以尊,臣子以顺,群生和洽,各按其性,此其作《易》垂教之本意也。
乾坤者,阴阳之本始,万物之祖宗,故为上篇之始而尊之也。离为日,坎为月,日月之道,阴阳之经,所以始终万物,故以坎离为上篇之终也,《咸》、《恒》者,男女之始,夫妇之道,人道之兴,必由夫妇,所以奉承祖宗,为天地之主,故为下篇之始而贵之也,《既济》《未济》为最终者,所以明戒慎而全王道也。
周子曰:圣人之精,画卦以示;圣人之蕴,因卦以发。卦不画,圣人之精不可得而见;微卦,圣人之蕴殆不可悉得而闻。《易》何止五经之原,其天地鬼神之奥乎!
邵子曰:天变而人效之,故“元亨利贞”。《易》之变也,人行而天应之,故“吉凶悔吝”。《易》之应也,以“元亨”为变,则“利贞”为应。以“吉凶”为应,则“悔吝”为变。元则吉,吉则利应之。亨则凶,凶则应之以贞。悔则古,吝则凶,是以变中有应,应中有变也。变中之应,天道也,故元为变,则亨应之;利为变,则应之以贞。应中之变,人事也,故变则凶,应则吉,变则吝,应则悔也。悔者吉之先,而吝者凶之本,是以君子从天不从人。
易有意象,立意皆所以明象。统下三者,有言象,不拟物而直言以明事;有像象,拟一物以明意;有数象,“七日”“八月”“三年”“十年”之类是也。
张子曰:大《易》不言有无,言有无,诸子之陋也。
《易》为君子谋,不为小人谋。故撰德于卦,虽爻有小大,及系辞其爻,必告以君子之义。
程子曰:有理而后有象,有象而后有数。得其义,则象数在其中矣。必欲穷象之隐微,尽数之毫忽,乃寻流逐末,术家之所尚,非儒者之所务也,管辂、郭璞之学是也。
理无形也,故因象以明理。理见乎辞矣,则可由辞以观象。故曰:得其义,则象数在其中矣。
看《易》且要知时,凡六爻人人有用,圣人自有圣人用,贤人自有贤人用,众人自有众人用,学者自有学者用,君有君用,臣有臣用,无所不通。
大抵卦爻始立,义既具,圣人别起义以错综之。如《春秋》前既立例,到后来书得全别,一般事便书得别有意思。若依前例观之,殊失之也。
作《易》者,自天地幽明,至于昆虫草木之微,无一而不合。
阴之道,非必小人也,其害阳则小人,其助阳成物则君子也。利非不善也,其害义则不善也,其和义则非不善也。
《传序》云:《易》,变易也,随时变易以从道也。其为书也,广大悉备,将以顺性命之理,通幽明之故,尽事物之情,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。圣人之忧患后世,可谓至矣。去古虽远,遗经尚存。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,后学诵言而忘昧。自秦而下,盖无传矣。予生千载之后,悼斯文之湮晦,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,此《传》所以作也。“《易》有圣人之道四焉,以言者尚其辞,以动者尚其变,以制器者尚其象,以卜筮者尚其占。”吉凶消长之理,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,推辞考卦,可以知变,象与占在其中矣。“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,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。”得其辞,不达其意者有矣。未有不得于辞,而能通其意者也。至微者理也,至著者象也,体用一源,显微无间。观会通以行其典礼,则辞无所不备。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,易于近者,非知言者也。予所传者辞也。由辞以得其意,则在乎人焉。
《易》之为书,卦爻彖象之义备,而天地万物之情见,圣人之忧天下来世其至矣。先天下而开其物,后天下而成其务。是故极其数,以定天下之象;著其象,以定天下之吉凶。六十四卦,三百八十四爻,皆所以顺性命之理,尽变化之道也。散之在理,则有万殊;统之在道,则无二致。所以“易有太极,是生两仪”。“太极”者道也,“两仪”者阴阳也。阴阳一道也,“太极”无极也。万物之生,“负阴而抱阳”,莫不有太极,莫不有两仪,絪緼交感,变化不穷,形一受其生,神一发其智,情伪出焉,万绪起焉,《易》所以定吉凶而生大业。故《易》者,阴阳之道也;卦者,阴阳之物也;爻者,阴阳之动也。卦虽不同,所同者奇偶。爻虽不同,所同者九六。是以六十四卦为其体,三百八十四爻互为其用。远在六合之外,近在一身之中。暂于瞬息,微于动静。莫不有卦之象焉,莫不有爻之义焉。至哉《易》乎!其道至大而无不包,其用至神而无不存。时固未始有一,而卦亦未始有定象。事固未始有穷,而爻亦未始有定位。以一时而索卦,则拘于无变,非易也。以一事而明爻,则窒而不通,非易也。知所谓卦爻彖象之义,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,亦非易也。故得之于精神之运,心术之动,与天地合其德,与日月合其明,与四时合其序,与鬼神合其吉凶,然后可以谓之知《易》也。虽然,《易》之有卦,易之已形者也。卦之有爻,卦之已见者也。已形已见者,可以言知。未形未见者,不可以名求。则所谓《易》者果何如哉?此学者所当知也。
朱子曰:《汉书》“易本隐以之显,《春秋》推见至隐”。易与《春秋》,天人之道也。《易》以形而上者,说出在那形而下者上。《春秋》以形而下者,说上那形而上者去。
问:《易》有“交易”,“变易”之义如何?曰:“交易”是阳交于阴,阴交于阳,是卦图上底,如“天地定位,山泽通气”云云者是也。“变易”是阳变阴,阴变阳,老阳变为少阴,老阴变为少阳,此是占筮之法,如昼夜寒暑屈伸往来者是也。
《易》是阴阳屈伸,随时变易,大抵古今有大阖辟,小阖辟,今人说《易》都无著摸,圣人便于六十四卦,只以阴阳奇偶写出来,至于所以为阴阳,为古今,乃是此道理。
圣人作《易》之初,盖是仰观俯察,见得盈乎天地之间,无非一阴一阳之理。有是理,则有是象。有是象,则其数便自在这里。非特河图、洛书为然,而图书为特巧而著耳。于是圣人因之而画卦。卦画既立,便有吉凶在里。盖是阴阳往来交错于其间,其时则有消长之不同。长者便为主,消者便为客。事则有当否之或异,当者便为善,否者便为恶。即其主客、善恶之辨,而吉凶见矣。故曰“八卦定吉凶”。吉凶既决定而不差,则以之立事,而大业自此生矣。此圣人作《易》,教民占筮,而以开天下之愚,以定天下之志,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。自伏牺而下,但有此六画,而未有文字可传。到得文王、周公,乃系之以辞。故曰“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”、大率天下之道,只是善恶而已,但所居之位不同,所处之时既异,而其几甚微,只为天下之人不能晓会,所以圣人因占筮之法以晓人,使人居则观象玩辞,动则观变玩占,不迷于是非得失之途。所以是书夏商周皆用之,其所言虽不同,其辞虽不可尽见,然皆太卜之官掌之,以为占筮之用。自伏牺而文王周公,虽自略而详,所谓占筮之用则一。盖即占筮之中,而所以处置是事之理,便在里了。故其法若粗浅,而随人贤愚皆得其用。虽是有定象,有定辞,皆是虚说此个地头,合是如此处置,初不黏著物上。故一卦一爻,足以包无穷之事,此所以见《易》之为用,无所不该,无所不遍,但看人如何用之耳。易如镜相似,看甚物来。都能照得。如所谓“潜龙”,只是有个“潜龙”之象,自天子至于庶人,看甚人来都使得。孔子说作龙德而隐,便是就事上指杀说来。然会看底,虽孔子说也活,也无不通。不会看底,虽文王周公说底也死了。须知得他是假托说,是包含说。假托,谓不惹著那事。包含,是说个影像在这里,无所不包。
易之有象,其取之有所从,其推之有所用,非苟为寓言也。然两汉诸儒,必欲究其所从,则既滞泥而不通。王弼以来,直欲推其所用,则又疏略而无据。二者皆失之一偏,而不能阙其所疑之过也。且以一端论之,乾之为马,坤之为牛,《说卦》有明文矣。马之为健,牛之为顺,在物有常理矣。至于案文责卦,若《屯》之有马而无乾,《离》之有牛而无坤,《乾》之六龙,则或疑于震,坤之“牝马”,则当反为乾,是皆有不可晓者。是以汉儒求之《说卦》而不得,则遂相与创为互体、变卦、五行、纳甲、飞伏之法。参互以求,而幸其偶合。其说虽详,然其不可通者,终不可通。其可通者,又皆傅会穿凿,而非有自然之势。唯其一二之适然而无待于巧说者,为若可信,然上无所关于义理之本原,下无所资于人事之训戒,则又何必苦心极力以求于此,而欲必得之哉!故王弼曰:义苟应健,何必乾乃为马;爻苟合顺,何必坤乃为牛?而程子亦曰:理无形也,故假象以显义。此其所以破先儒胶固支离之失,而开后学玩辞玩占之方,则至矣。然观其意又似直以《易》之取象,无复有所自来,但如《诗》之比兴,孟子之譬喻而已。如此则是《说卦》之作,为无所与于易。而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”者,亦剩语矣。故疑其说亦若有未尽者,因窃论之,以为《易》之取象,固必有所自来,而其为说,必已具于太卜之官,顾今不可复考,则姑阙之。而直据辞中之象,以求象中之意,使足以为训戒,而决吉凶。如王氏、程子与吾《本义》之云者,其亦可矣。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来,然亦不可直谓假设,而遽欲忘之也。
《易》之象似有三样:有本画自有之象,如奇画象阳、偶画象阴是也;有实取诸物之象,如乾坤六子,以天地雷风之类象之是也;有只是圣人自取象来明是义者,如“白马翰如”、“载鬼一车”之类是也。
易有象辞,有占辞,有象占相浑之辞。
问:王弼说初上无阴阳定位,如何?曰:伊川说阴阳奇偶,岂容无也?《乾》上九“贵而五位”。《需》上六不当位,乃爵位之位,非阴阳之位,此说最好。
《易》只是为卜筮而作,故《周礼》分明言太卜掌三《易》: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、《周易》。古人于卜筮之官,立之凡数人。秦去古未远,故《周易》亦以卜筮得不焚。今人说《易》是卜筮之书,便以为辱累了易。见夫子说许多义理,便以为《易》只是说道理,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,而其教人之意无不在也。今人却道圣人言理,而其中固有卜筮之说,他说理后,说从那卜筮上来作么?
上古之时,民心昧然,不知吉凶之所在。故圣人作《易》,教之卜筮,使吉则行之,凶则避之。此是开物成务之道。故《系辞》云:“以通天下之志,以定天下之业,以断天下之疑”,正谓此也。初但有占而无文,往往如今之环环相似耳。今人因《火珠林》起课者,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辞,则知古者之占,往往不待辞而后见吉凶。至文王周公,方作彖爻之辞,使人得此爻者,便观此辞之吉凶。至孔子,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,故又复逐爻解之。谓此爻所以吉者,谓以中正也。此爻所以凶者,谓不当位也。明明言之,使人易晓耳。至如《文言》之类,却是就上面发明道理,非是圣人作《易》,专为说道理以教人也。须见圣人本意,方可学易。
圣人作易,本是使人卜筮,以决所行之可否,而因之以教人为善。如严君平所谓与人子言依于孝,与人臣言依于忠者。故卦爻之辞,只是因依象类,虚设于此,以待叩而决者,使以所值之辞,决所疑之事。似若假之神明,而亦必有是理而后有是辞。理无不正,故其丁宁告戒之辞,皆依于正。天下之动,所以正夫一,而不谬于所之也。
卦爻之辞,本为卜筮者断吉凶,而因以训戒。至《彖》、像》、《文言》之作,始因其吉凶训戒之意,而推说其义理以明之。后人但见于孔子所说义理,而不复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。因鄙卜筮为不足言,而其所以言《易》者,遂远于日用之实,类皆牵合委曲,偏主一事而言,无复包含该贯曲畅旁通之妙。若但如此,则圣人当时,自可别作一书,明言义理,以诏后世。何用假托卦象,为此艰深隐晦之辞乎?
大抵《易》之书,本为卜筮而作,故其辞必根于象数,而非圣人己意之所为。其所劝戒,亦以施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,而非反以戒夫卦爻者。近世言《易》者,殊不如此,所以其说虽有义理,而无情意。虽大儒先生,有所不免。比因玩索,偶幸及此,私窃自庆,以为天启其衷,而以语人,人亦未见有深晓者。
《易》中都是贞吉,不曾有不贞吉;都是利贞,不曾说利不贞。如占得《乾》卦,固是大亨,下则云“利贞。盖正则利,不正则不利。至理之权舆,圣人之至教,寓其间矣。大率是为君子设,非小人盗贼所得窃取而用。
蔡氏元定曰:天下之万声,出于一阖一辟。天下之万理,出于一动一静。天下之万数,出于一奇一偶。天下之万象,出于一方一圆。尽起于乾坤二画。
许氏衡曰:初,位之下,事之始也,以阳居之,才可以有为矣。或恐其不安于分也,以阴居之,不患其过越矣。或恐其软弱昏滞,未足以趋时也。大抵柔弱则难济,刚健则易行。或诸卦柔弱而致凶者,其数居多。若总言之,居初者,易贞。居上者,难贞。易贞者,由其所适之道多。难贞者,以其所处之位极。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,而上每有不可救者。始终之际,其难易之不同盖如此。
二与四,皆阴位也:四虽得正,而犹有不中之累,况不得其正乎?二虽不正,而犹有得中之美,况正而得中者乎?四,近君之位也。二,远君之位也。其势又不同。此二之所以“多誉”,四之所以“多惧”也。二中位,阴阳处之,皆为得中。中者,不偏不倚、无过不及之谓。具才若此,故于时义为易合。时义既合,则吉可断矣。
卦爻六位,惟三为难处。盖上下之交,内外之际,非平易安和之所也。
四之位近君,“多惧”之地也。以柔居之,则有顺从之美。以刚居之,则有僭逼之嫌。然又须问,居五者,阴邪阳邪?以阴承阳,则得于君而势顺。以阳承阴,则得于君而势逆。势顺则无不可也,势逆则尤忌上行,而凶咎必至。以阳承阳,以阴承阴,皆不得于君也。然阳以不正而有才,阴以得正而无才,故其势不同。有才而不正,则贵于寡欲,故乾之诸四,多得免咎。无才而得正,则贵乎有应,故艮之诸四,皆以有应为优,无应为劣。独坤之诸四,能以柔顺处之,虽无应援,亦皆免咎。此又随时之义也。
五,上卦之中,乃人君之位也。诸爻之德,莫精于此。能首出乎庶物,不问何时,克济大事。《传》谓五“多功”者此也。
上,事之终,时之极也。其才之刚柔,内之应否,虽或取义,然终莫及上与终之重也。是故难之将出者,则指其可由之方。事之既成者,则亦以可保之道。义之善或不必劝,则直云其吉也。势之恶或不可解,则但言其凶也。质虽不美,而冀其或改焉,则犹告之。位虽处极,而见其可行焉,则亦谕之。大抵积微而盛,过盛而衰,有不可变者,有不能不变者。《大传》谓“其上易知”,岂非事之已成乎?
胡氏一桂曰:上下体虽相应,其实阳爻与阴爻应,阴爻与阳爻应,若皆阳皆阴,虽属相应之位,则亦不应矣。然事固多变,动在因时,故有以有应而得者,有以有应而失者,亦有以无应而吉者,有以无应而凶者,斯皆时事之使然,不可执一而定沦也。至若《比》五以刚中,上下五阴应之;《大有》五以柔中,上下五阳应之;《小畜》四以柔得应,上下五刚亦应之,又不以六爻之应例沦也。
六十四卦皆以五为君位者,此《易》之大略也。此间或有居此位而非君义者,有居他位而有君义者,斯易之变,不可滞于常例。
胡氏炳文曰:《易》卦之占,亨多,元亨少。爻之占,吉多,元吉少。元亨,大善而亨。元吉,大善而吉也。人之行事,善百一,大善千一,故以元为贵。然兹事也,请论心之初。善不善,皆自念虑之微处,充之即是。此善之最大处,盖有一毫之不善,非元也。有一息之不善,非元也。
吴氏澄曰:时之为时,莫备于《易》。程子谓之随时变易以从道。夫子《传》六十四《彖》,独于十二卦发其凡,而赞其时与时义、时用之大,一卦一时,则六十四时不同也。一爻一时,则三百八十四时不同也。始于《乾》之《乾》,终于《未济》之《未济》,则四千九十六时,各有所值。引而伸,触类而长,时之百千万变无穷,而吾之所以时其时者,则一而已。
薛氏瑄:六十四卦,只是一奇一偶。但因所遇之时,所居之位不同,故有无穷之事变。如人只是一动一静,但因时位不同,故有无穷之道理。此所以为《易》也。
蔡氏清曰:《乾》卦卦辞,只是要人如《乾》。《坤》卦卦辞,只是要人如《坤》,至如《蒙》、《蛊》等卦,则又须反其义。此有随时而顺之者,有随时而制之者。易道只是时。时则有此二义,在学者细察之。
周公之系爻辞,或取爻德,或取爻位,又或取本卦之时与本爻之时,又或兼取应爻,或取所承、所乘之爻。有承、乘、应与时位兼取者,有仅取其一二节者,又有取一爻为众爻之主者。大概不出此数端。
上一章节
下一章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