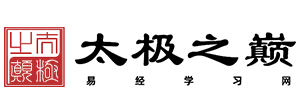《易图讲座》·第28讲 明代的易图:韩邦奇的《易学启蒙意见》
韩邦奇(1479一1555年),字汝节,号苑洛,朝邑(今陕西大嘉)人。正德戊辰(1508年)进士,官至南京兵部尚书,谥恭简。弘治十六年(1503)著《易学启蒙意见》四卷,又有《见闻考随录》五卷。
《易学启蒙意见》为照录朱熹《易学启蒙》全文并加入衍图和“意见”之书。卷一“本图书第一”、“原卦画第二”,就朱熹十数《河图》衍出三十三图,九数《洛书》衍出二十三图,就朱熹六横图衍出二图,将《伏羲六十四卦方位》图分作圆、方二图(此乃本朱熹“将方图取出放外”说而作);卷二“明蓍策第三”,本文之中有“易筮序略”、“筮仪”(今见于《原本周易本义》内容,实为原本《易学启蒙》内容)和衍图四十余幅(所录本文有与今见《易学启蒙》有不同之处);卷三、卷四“考占变第四”,以朱熹所述“七占”变例各附卦变图:“凡卦六爻皆不变,则占本卦彖辞”之例,附以朱熹起《乾》终《坤》大横图,每卦之下标以所占“本卦彖辞”;“一爻变则以本卦变爻辞占”之例,附六十四卦每卦各变六卦之图;“二爻变则以本卦二变爻辞占”一例,附六十四卦每卦二个爻变所得卦图;“三爻变则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辞”二例,附六十四卦每卦三个爻变所得卦图;“四爻变则以之卦二不变爻占”之例,附六十四卦每卦四个爻变所得卦图;“五爻变则以之卦不变爻占”之例,附六十四卦每卦五个爻变所得卦图;“六爻变则乾坤占二用余占之卦彖辞”之例,附六十四卦每卦六个爻变所得卦图。又于辨朱熹“以事理推之”占法“犹有可疑”而加“七占’’新法意见之后,列朱熹三十二幅变占图之第一图,加列三十二幅“加详”图。
在韩氏诸多衍图之中,惟其据“夫造化者数而已矣,五十者,造化之体也,四十有九者,造化之用也,四使有九者,万物之体也,四十有八者,万物之用也。是故五十而去一,维天之命,于穆不已者也;四十九而去一,万物各正性命者也。用九用八之不同,其神化之谓乎?”一段本文(此段文字不见于今本《易学启蒙》)衍出之二图(见下图),可谓新奇之图。韩氏注曰:“此节何以不用濂溪之图?夫为图所以立象也。阴阳五行万物不在天地之外,阴阳有渐,无遽寒遽热之理。知觉运动,荣瘁开落,卵亥之化也。”此图乃本胡一桂《文王十二月卦气图》演变而来,而胡一桂之图又明显据“十二月卦”圆图演变而得。所以,究其本当出于孟喜之“十二月卦”说(今见最早将十二月卦画做圆图者,则出彭晓《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》所列《明镜图》)。
韩邦奇之书命曰“意见”,是诠释朱熹《易学启蒙》同时阐述个人见解之书。因其是述解朱熹易学思想之书,成书后即有“大巡周公”命梓,“大司马韩公”为序,“节推东公”校正,“平阳府同知李沧”刊刻,则见明代中叶是书影响之不同一般。其实,一部通解《易学启蒙》“小书”之书之所以有如此影响,亦是当时“形势使之然耳”。朱熹序《易学启蒙》曰:“近世学者,类喜谈易,而不察乎此,其专于文义者,既支离散漫,而无所根著;其涉于象数者,又皆牵合附会,而或以为出于圣人心思智虑之所为也。若是者,予且病焉。因与同志颇辑旧闻,为书四篇,以示初学,使勿疑于其说云。”后之人则认为朱熹“以示初学”是谦辞,而《易学启蒙》一书遂有“不刊之书”的美誉。至明代,朱熹易学被定为官方易学,《周易本义》与《易学启蒙》即成为文人士子科考进阶必读之书,于此形势之下,一部《易学启蒙意见》则成为人们为仕途奋斗而必备的参考书了。
事实上,韩邦奇通释《易学启蒙》,并非完全合于朱熹本意。其一,韩氏曰:“伏羲与邵子同加一倍也,孔子则相荡也”,谓后儒失“先天之义,微微之旨”,则是因“自夫子称相荡”始。朱熹尝曰:“在四象生八卦以上,便是圣人本意底“(《朱子语类》卷六十六),按此说,孔子《系辞》“易有太极”一节即是说圣人一奇一偶“加一倍”画八卦,即韩氏所诣“先天者,加一倍者也”。而《系辞》又曰“八卦相荡”、“因而重之”,《说卦》又曰“八卦相错”,《周易本义》释为“八相荡而为六十四”,即是说八卦至六十四卦,不是由“加一倍法”而来。如此则孔子既言“加一倍”又言“相荡”,如何后儒会因“自夫子称相荡”而失“先天之义微微之旨”?《易学启蒙》本“易有太极”一节之义而出六横图,则“先天者加一倍”出于《系辞》似无疑意,是孔子代先圣而言“先天加一倍”。所以,朱熹之《易学启蒙》中并无韩氏所谓之意思。其二,《易学启蒙》仅列《文王八卦图》,《周易本义》列《文王八卦次序》、《文王八卦方位》,而韩氏则准《序卦》自作《文王六十四卦图》,图后全文录出《序卦》原文,注曰:“此明文王改易伏羲六十四卦之次也。”此则亦出朱熹本意之外。朱熹以《序卦》为“非圣人之精”,尝谓《序卦》有“不可晓处”,故于《周易本义》只录《序卦》本文,而不加任何疏解(只有区区“晁氏曰郑无而泰而字”九字之注),至于文王之卦“则熹尝以卦画求之,纵横反复,竟不能得其所以安排之意,是以畏惧,不敢妄为之说”(《答袁枢》),而韩氏则反其道而行之。其三,韩氏曰:“七占之法不传久矣,朱子以事理推之于前,然犹有可疑者。”于是便把朱熹所定“七占之法”更定了四条。其所更定之法,似有见于《彖传》。其四,韩氏谓《易学启蒙》说三爻变时所引“沙随程氏曰,晋公自重耳筮得国,遇贞屯悔豫皆八”之例,是“此史氏之失职也,而援以为证,过矣”。其五,韩氏曰:“即其图观之,冲漠无朕之际,五十有五之数已具于十五之中矣,是所谓太极也。及其五十有五之数形布互错于十五之外,一三其七为阳,二四六八为阴,所谓两仪也。”此以五十五数为太极全体之数说,与朱熹“河图之虚五与十者,太极也“之说不同。以上数例可证,韩氏虽自谓“理则吾莫如之何也”,但在“一为太极”、“理一分殊”在个理上,却与朱熹有所不同。
易图书学发展至明代中期而有《易学启蒙意见》一书,此书虽是通释之作,然而的确参有作者个人“意见”。这些“意见”内容有着时代特点,反映出当时学者对朱熹《易学启蒙》的理解水平。其中涉及八卦来源这一根本问题,《系辞》本言圣人仰观俯察远求近取以作八卦,而以“河出图、洛出书”为“天生神物”,所谓“圣人则之”者,并无明言所则为何事,以《观·彖》“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,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”之语分析,所谓“天生神物”即天之神道,盖圣人本“河出图,洛出书”之神话传说,只不过是以“神道设教”而已。可是《易学启蒙》却专以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为圣人画卦之本,实在是不能脱自谓“其涉于象数者,又皆牵合附会”之巢臼,而《易学启蒙意见》又津津乐道于此,从中衍出五十多幅黑白点数图,则见当时儒生囿于封建思想禁锢,易图学研究之固陋。
韩邦奇之《易学启蒙意见》一书,其中所录《易学启蒙》文字有与今见本不同之内容,而今见本《易学启蒙》内容又与清康熙年间成书之《御纂周易折中》中《易学启蒙》完全相同,则知后人对朱熹原本《易学启蒙》有所更动。考朱熹《易学启蒙》之原貌,韩邦奇此书可引为参考。
韩邦奇所作中空如“黑白两条蚯蚓”环绕之图,对后来人有一定的影响,来知德之《梁山来知德圆图》即是此图的翻版。以此图可知,所谓“古太极图”之黑白鱼形图之本源与之不同。